
□赵瑞霖
此刻,夕阳西下。不过并没有断肠人,倒是有一只花蜻蜓停在我家的纱窗上。我打开窗子,伸手想要去捉住它。可是,它动作敏捷,扇动着翅膀一溜烟飞走了。
好似城里的虫子都是这般聪明。比如叮了你一整夜的蚊子,你愣是打不着;绕灯三周半的蛾子,你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在房间里飞来飞去的苍蝇,你追都追不上。
在乡村的虫子可就容易捉到得多了,徒手或是用网兜、苍蝇拍都可以。所以,单单是这个原因,也让我无限怀念乡村的昆虫。
蚊子、苍蝇、天牛,这三种昆虫是我天生的死对头,遇到它们,我必诛之。
炎热的夏夜,打开风扇,躺在凉席上,刚刚进入梦乡。几只不识趣的蚊子就开始骚动起来,在我的脸上、手臂上、脚面上停歇下来。我知道,它们是要伺机插入“针管”吸我的血。我一个巴掌过去,蚊子便血肉模糊,真是大快人心。如果它们成群结队来,我也有办法,烧蚊香喷蚊香液涂防蚊水。总之,这些蚊子定是有来无回。
而对付苍蝇,则需要伺机而动。我手握苍蝇拍,收紧胳膊蓄力。同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当听到扇动翅膀“嗡嗡嗡”的声音,就表示苍蝇来了。循声望去,它正伏在桌上,想去一尝饭菜的香味。这时,我眼疾手快,一个大力正手拍外加90度回旋,这只惹人厌的苍蝇,在桌上“肠穿肚烂”,伸腿瞪眼地进行死前最后的挣扎。
天牛在我们这里俗称“马牯牛”,也是一种害虫,它们啃食树木。它们的种类繁多,颜色各异,据说有几千种。我们这里黑色白点的马牯牛居多,也有黄色和红颈马牯牛。它们的幼虫都生活在树木里,这个自然我是捉不到的。不过“恶人自有恶人磨”,管氏肿腿蜂是马牯牛幼虫的天敌,我们这些孩子则是成虫的克星。
成虫后的马牯牛会选择一些低矮的树木栖息,继续取食花粉或啃食嫩枝。好在它们不善飞行,只能近距离地飞腾,只要手快,一把钳住颈部或是触角,它便束手无策,只能任人宰割了。捉到马牯牛后,我会找一些坚硬的金属或石子诱它使用上颚啃咬,颇有一种“看你的嘴有多硬”的意味。虽说马牯牛号称“锯树郎”,但让我如此操作一番,没几个回合它就败下阵来。上颚损毁严重的马牯牛再也不能“行凶作恶”了,等待它的只有死亡。
那时我就有了“对付害虫,决不能姑息”的理念。如果你不将它们杀死,那么受害的往往会是人类自己。相反,如果是益虫,诸如七星瓢虫、螳螂、蜜蜂等绝对是值得保护的。
第一次看到七星瓢虫,是在幼年的图画书上,色彩艳丽并且有着斑点,让我大开眼界。我在我家小菜园的蔬菜上找寻,果真找到了几只七星瓢虫。它们在菜园里翩翩起舞,煞是好看。七星瓢虫以蚜虫为食,有时还取食小土粒、真菌孢子和一些小型昆虫,秋天还常常取食植物的花粉。但除了七星瓢虫,其他瓢虫绝非都是“好货色”,它们以树叶、草叶为食,喜欢庄稼新鲜的嫩叶,和蚜虫的可恶之处并无区别。瓢虫善恶不一,倒也是让人喜忧参半。
说了这么多昆虫,我最喜欢的还是螳螂。因为它气宇轩昂,一副雄赳赳的模样让我着迷。看过《精灵宝可梦》里面的飞天螳螂后,我对螳螂更情有独钟了。
成年螳螂体长大约10公分,浑身翠绿,就像一片柳树的叶子。身后有一对膜翅,有的透明,有的呈棕色,还有的与身体融为一色,绿油油的。它的前肢是两把“大刀”,上有一排坚硬的锯齿,末端各有一个钩子,用来钩住猎物。我目睹过螳螂捕食,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扑向蝗虫,用那对“大剪刀”狠命钳住对方。没过多久,蝗虫就一命呜呼了。
早在多年前人们就对螳螂捕食动作进行过细致观察,创造出了著名的螳螂拳。其拳法正迎侧击、虚实相应、长短兼备、刚柔相济、手脚并用,使人难以捉摸,防不胜防;用连环紧扣的手法直逼对方,使敌无喘息机会。由此可见,螳螂是一个真正的“武术家”。
我想,每个人都有印象较为深刻的虫事,像是勤劳勇敢的蜜蜂、叫唤不停的知了、漫天飞舞的蝴蝶、好勇斗狠的蟋蟀、集结成列的蚂蚁、织网吐丝的蜘蛛、毒性极强的蝎子等等。正是有了无数这样的小生灵陪伴在我们身边,让我们的生活多了更多的故事,添了更多的滋味。

山野 汤青 摄
□王月英
终于有机会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老家。
整个村子变得漂亮时尚,整齐划一的白墙蓝瓦的砖房,太阳能路灯笔直地立在水泥道两旁,村小学改建成了休闲广场,连家家户户门前的菜园子都让出一半,变成了停车场。遗憾的是,小时候常见的鸡鸭鹅不见了,路上没有上蹿下跳的淘小子们,更看不到挎着篮子去河边洗衣服的姑娘。
这和我梦中的故乡不一样了。
梦里的故乡屋前屋后有各类蔬菜、果树,有孩子们下河摸鱼上树掏鸟蛋的身影,有在地里锄草的汗水,更有村东头大片塔头甸子里的哈糖果朝我招手。
恍然间又回到了儿时的暑假。村前村后玩腻的我们,总会约着向东,向七八里外的乌苏里江挺进。想去隔江看看对面有没有人家,想去验证一下江边的沙滩是不是金色的。
行走在乡间小路上,其左侧就是一望无际的塔头甸子,现在被称为湿地。塔头上生长着一丛丛灌木。一到夏天,那灌木树丛里的果子就会变紫,果子形如瘦长的灯笼,外面裹着一层白霜,托盘是红色的,摘一颗放嘴里,酸酸甜甜,特别解渴,比曹操的望梅止渴管用得多。我们当地人称它为“哈糖果”,其实人家有大名的,叫蓝莓。
从江边往回返时,碰到哈糖果时会把褂子脱下,两个袖子捆在腰上,扯起后身衣角,兜着摘下来的哈糖果,屁颠屁颠往家跑。回到家后,找一个罐头瓶子,把哈糖果塞进去,放上点白糖,扣上盖,藏到厦子里。过几天取出来吃,那股子酸甜劲至今还留在唇齿间。
当然,有时被染紫的褂子会暴露哈糖果的存在,一顿胖揍是肯定跑不了的。因为大人们绝对禁止我们小孩擅自去塔头甸子的,那里的沼泽地会吃人。
小学毕业那年的暑假,镇上有人高价收哈糖果,说是可以出口,外国人拿去做饮料。我想去挣学费,再三央求下,父亲终于答应带我去草甸子里摘哈糖果。父亲在前面领路,试探着踩那些结实的塔头,以防掉进沼泽地里。有父亲在,就不会有危险。我拎着水桶,穿着水靴子,特别坦然地跟在父亲后面,东张西望地寻找着哈糖果。哈糖果喜欢热闹,遇到就是一大片。桶里的哈糖果越来越多,我的上学梦越做越远。
如今,却再也寻不到塔头甸子,再也摘不到那酸酸甜甜的哈糖果。我暗自思量,如果自己一直在,一直陪伴着哈糖果,是不是结果就不一样呢。其实也未必,只是不同的选择带来不同的失落罢了。

□晴澜
清晨,我下楼去散步。清明时节,空中飘着霏霏细雨,如丝般冰凉光滑,细密地滑过裸露的肌肤,打湿了头发,沾了衣裳。我没有撑伞,也没戴帽子,穿着短衣短裤,任由雨点打在皮肤上。
空气清冽甘甜,还有些淡薄的凉意。黑白灰在天空随意泼洒,变幻成无数的国画,意境深邃,灵动飘逸。空中积压着厚厚的灰色云层,感觉随时会来一场“哗啦啦”的大雨。但是大雨一直未来,是不是因为春风使劲儿吹?吹啊,吹得大树“哗哗”响,吹得满地落英,也吹散了乌云。天空时而明亮,时而乌黑,那是风与云在快乐地游戏、相恋吧?
最喜欢小区的人工湖了。天空时时变幻,湖水随时应和。乌云飘过来时,湖面是灵动的中国画;春风不时撩拨她的心弦,湖水快乐地颤动,荡起阵阵涟漪。
这个时节,最快乐的莫过于花草树木了。如油的春雨滋润着它们,生机勃发。小草上贴附着雨珠,花朵上滚动着雨珠,树上悬挂着雨珠,万物好像都痴迷着雨。新的小草长出来了,毛茸茸的,一小片、一大片伸展开来,温柔、坚定地茂密生长。新叶长出来了,老叶还未脱落,各种层次的绿竞相展示,有浓有淡,或明或暗:浅绿、嫩绿、深绿、暗绿;或者糅杂了其他颜色:青绿、碧绿、黄绿、褐绿,真是绿色主宰的时节。
每个清晨当属鸟儿最快乐,沉寂了一整夜,东方稍亮,它们就欢腾起来,尽情歌唱。处处闻及鸟鸣,清脆尖厉的,温柔浅唱的,还有布谷鸟的声音“李贵娘”,最是特别,婉转悠扬,又似透着无尽的忧伤。小时候,妈妈告诉我一个悲伤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女人名叫李贵娘,因被婆婆嫌弃而投河自尽。其丈夫听到消息后,忧郁悲痛而死,化为布谷鸟,在每一个春天来临时,一遍一遍呼唤她的名字。
转过一处屋角,传来缕缕幽香,绵密又浓烈,只见洁白温润的栀子花挺立枝头。每每看到它们,就会想起逝去30年的外婆,从前在这个季节,经常为我做独特美味的栀子花鸡蛋汤。我闭上双眼,站在树前,浓浓的花香就像外婆的爱,紧紧包绕着我。外婆,那个最爱我的人,如今躺在千里之外的坟茔里。外婆,您的爱一直鼓舞和感染我,我很快乐和感恩。
这是一个雨的时节,绿的时节;也是思念的时节,爱的时节。


□侯淑荷
近日,看到一个令我触动的视频。吉林通化的一位女子,在收拾母亲遗物时,意外发现一个装满银杏叶的信封,打开之后发现,是母亲在父亲去世的十年里,每到父亲忌日那天,她都会去经常与父亲散步的路上,捡一枚银杏叶,然后在银杏叶上写满对父亲的思念。
这些记满思念的银杏叶深深打动了我,也让我的思绪回到公婆生病的那段难忘的时光。公婆身体一直很硬朗,6年前的一天,公公突然感觉身体不适,我们带老人到大医院检查身体,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公公进入医院以后就没能够再出来。
公公是做地质工作的,天南海北地走,婚后与婆婆聚少离多,后来又入伍到了新疆,更是几年也回不了一次家。公公家贫,他少年丧父,又是家中长子,公公离家在外,婆婆要帮助照顾一家老小,还要干繁重的农活,婆婆生四个孩子的时候,公公都不在身边。婆婆吃了很多常人无法想象的苦,却从来不大提这些。
公公住院的日子里,婆婆每日念叨说:“老爷子常年锻炼身体,从来没得过什么大病,体质好,一定会没事的。”又说:“不求他能像原来那样健康,只要能回来,天天看着他,照顾他,给他做饭吃,我就心满意足了。”
记得端午节那天,公公已经病得很重了,家人都在医院陪护公公,我在家陪婆婆过节。清早,我早早出去买回了艾蒿和鲜艳的葫芦,挂在了公婆的房门上,那天婆婆很高兴,一直说:“你这孩子有心,‘葫芦’冲一冲你爸爸病就好了,就能回家了。”
只是,令人遗憾的是,公公在医院的全力抢救之后,还是离开了。
公公离开以后,我们怕婆婆孤单,家里一直留人陪伴着她,和她聊天,劝慰伤心中的她。尽管这样,公公离开不久,婆婆因为思虑过度还是得了重病住进了医院里。幸运的是抢救及时,婆婆在医院调养一段时间以后康复了。
婆婆回到家以后,依旧满眼都是忧伤,公公不在的家,处处都是公公的影子。无论我们怎么开导婆婆,她都郁郁寡欢,常常一个人流泪。转眼到了中秋节,早晨婆婆精神尚好,只是言语间都是对公公的想念。婆婆说:“老爷子一辈子都不会做饭。过节了,他一定很孤单。”说着说着又流下泪来。我们劝慰了好一会,婆婆心情才好些。
和婆婆在阳台上聊了一会天,婆婆说有些累了,我们扶着婆婆回房间休息。爱人开始在厨房准备节日的午餐。不一会,婆婆叫在厨房做饭的爱人说:“儿子,我有些不舒服。”爱人急忙跑到房间一手扶着她坐在床上,一手拨打120。这时,婆婆拉住爱人的手说:“儿子,我不去医院。”谁能想到,这就是婆婆说的最后一句话,疾驰而来的120也没能挽回婆婆的生命。就这样,婆婆离我们而去了,与公公离世只相隔85天。那是一个没有明月的中秋节,让我们这些孩子从此走失了回家的路。
有时候,我们会想,一定是婆婆怕公公一个人过节太冷清了,才舍得抛弃她疼爱的儿女去找公公团聚去了。每次想起公婆,我的心里都充满了思念和感动,思念两位可亲可敬的老人,感动他们淳朴至真的爱情。

□查晶芳
我每次上早读课,在街角等车,总是看见那个老人。他拿着大扫帚,一边忙碌,一边唱歌,声音不大,但很欢快。
第一次见他是在前年深冬的一个早晨。我紧赶慢赶6点25分下了楼,外面还黑漆漆的,一个人影也没有。唉,这么冷的天起这么早,大概只有我们当教师的吧。心里嘀咕着,脚下可不敢怠慢,一路小跑,往街口赶校车。
咦,远远听到前面有人在唱歌。越来越近,听到词了:“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劳动,为她打扮,为她梳妆……”嗓音虽然有些沙哑,但中气还挺足,情感也很投入。这是谁呀?拐过街角,一个橘黄的身影映入眼帘。原来是一名环卫工人,和我一样,也在赶早上班呢。他看上去年近花甲,矮矮瘦瘦的,宽大的工作服套在身上显得空空荡荡,如果把他手中那大扫帚竖起来,估计和他差不多高。他边扫边唱,见我看着他,有点不好意思,停了歌声,对着我微微一笑。我也冲他略一点头,转身上了车。车启动了,橘黄色的身影越来越小,那歌声却好像并未远去。
从那以后,每周上早读课我都能碰到他。时间一长,我们成熟人了。每次,他依然是挥着扫帚,哼着歌,唱得最多的就是《在希望的田野上》。有时,他看见我在跑,就会暂停歌声,对着我喊:“车还没走,不要急的哦。”看我气喘吁吁地站定,他便露出慈祥的笑容。有一次他还说:“你们当老师的不容易,要起这么早,还天天要费心费神,现在的小鬼不好教呢。”我说他也辛苦,他连连摆手:“我只要把地扫干净了,心里就亮堂了,不烦其他神呢。”他弓下身子,背着双手,眼睛盯着扫过的地面,慢慢巡视一圈。像指甲大的碎纸片、寸许长的细棍子等这些“漏网之鱼”全逃不过他的法眼,将它们“就地正法”后,他才哼着歌坐下歇会儿。
有一次,我忍不住说:“您唱得挺好的呀。”见我夸他,他很意外,略显羞涩:“我瞎唱唱呢。”嘴里谦虚着,满脸的皱纹却笑出了深沟。我问他咋这么喜欢唱这首歌。“这歌好。唱的就是我们农村的事,田埂、小河、麦子、高粱、插秧,还撒网打鱼,我一唱做事更有劲。”老人笑咪咪地絮叨着,我也忍不住笑了。
一天早晨,我正准备上车,看到一名匆匆忙忙的路人在马路正中弄翻了拎在手里的早点,面条和着汤水洒了一地。那人跺脚嘟囔着:“唉,大清早把饭泼了。”蹲下身准备收拾。当时,老人刚扫完地坐着休息,快步走过去说:“我来搞,你忙你的去。”那人连声说抱歉,老人摆摆手:“麻烦个啥,本来就是我应当做的事。”
我原以为老人这么大年纪还做环卫工人,不是经济困窘就是儿女不孝。那天校车晚点了,我和老人聊了一会儿家常,得知他的两个儿子在城里“混得都蛮好”,对他也关心照顾得很,早就不同意老父亲做这份工作了,但老人自己执意要做。“这事情做习惯了,不做还真难受。也怪,我歇在家里总是这痛那痒的,后来知道这路段缺人,就来了。你别说,一做事那些毛病全都好了。”老人看着马路的眼神满是喜悦,像对着自己的孩子般深情。
“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人们在明媚的阳光下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变样……”老人又欢快地唱起来了。
□张勇


□赵瑞霖
此刻,夕阳西下。不过并没有断肠人,倒是有一只花蜻蜓停在我家的纱窗上。我打开窗子,伸手想要去捉住它。可是,它动作敏捷,扇动着翅膀一溜烟飞走了。
好似城里的虫子都是这般聪明。比如叮了你一整夜的蚊子,你愣是打不着;绕灯三周半的蛾子,你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在房间里飞来飞去的苍蝇,你追都追不上。
在乡村的虫子可就容易捉到得多了,徒手或是用网兜、苍蝇拍都可以。所以,单单是这个原因,也让我无限怀念乡村的昆虫。
蚊子、苍蝇、天牛,这三种昆虫是我天生的死对头,遇到它们,我必诛之。
炎热的夏夜,打开风扇,躺在凉席上,刚刚进入梦乡。几只不识趣的蚊子就开始骚动起来,在我的脸上、手臂上、脚面上停歇下来。我知道,它们是要伺机插入“针管”吸我的血。我一个巴掌过去,蚊子便血肉模糊,真是大快人心。如果它们成群结队来,我也有办法,烧蚊香喷蚊香液涂防蚊水。总之,这些蚊子定是有来无回。
而对付苍蝇,则需要伺机而动。我手握苍蝇拍,收紧胳膊蓄力。同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当听到扇动翅膀“嗡嗡嗡”的声音,就表示苍蝇来了。循声望去,它正伏在桌上,想去一尝饭菜的香味。这时,我眼疾手快,一个大力正手拍外加90度回旋,这只惹人厌的苍蝇,在桌上“肠穿肚烂”,伸腿瞪眼地进行死前最后的挣扎。
天牛在我们这里俗称“马牯牛”,也是一种害虫,它们啃食树木。它们的种类繁多,颜色各异,据说有几千种。我们这里黑色白点的马牯牛居多,也有黄色和红颈马牯牛。它们的幼虫都生活在树木里,这个自然我是捉不到的。不过“恶人自有恶人磨”,管氏肿腿蜂是马牯牛幼虫的天敌,我们这些孩子则是成虫的克星。
成虫后的马牯牛会选择一些低矮的树木栖息,继续取食花粉或啃食嫩枝。好在它们不善飞行,只能近距离地飞腾,只要手快,一把钳住颈部或是触角,它便束手无策,只能任人宰割了。捉到马牯牛后,我会找一些坚硬的金属或石子诱它使用上颚啃咬,颇有一种“看你的嘴有多硬”的意味。虽说马牯牛号称“锯树郎”,但让我如此操作一番,没几个回合它就败下阵来。上颚损毁严重的马牯牛再也不能“行凶作恶”了,等待它的只有死亡。
那时我就有了“对付害虫,决不能姑息”的理念。如果你不将它们杀死,那么受害的往往会是人类自己。相反,如果是益虫,诸如七星瓢虫、螳螂、蜜蜂等绝对是值得保护的。
第一次看到七星瓢虫,是在幼年的图画书上,色彩艳丽并且有着斑点,让我大开眼界。我在我家小菜园的蔬菜上找寻,果真找到了几只七星瓢虫。它们在菜园里翩翩起舞,煞是好看。七星瓢虫以蚜虫为食,有时还取食小土粒、真菌孢子和一些小型昆虫,秋天还常常取食植物的花粉。但除了七星瓢虫,其他瓢虫绝非都是“好货色”,它们以树叶、草叶为食,喜欢庄稼新鲜的嫩叶,和蚜虫的可恶之处并无区别。瓢虫善恶不一,倒也是让人喜忧参半。
说了这么多昆虫,我最喜欢的还是螳螂。因为它气宇轩昂,一副雄赳赳的模样让我着迷。看过《精灵宝可梦》里面的飞天螳螂后,我对螳螂更情有独钟了。
成年螳螂体长大约10公分,浑身翠绿,就像一片柳树的叶子。身后有一对膜翅,有的透明,有的呈棕色,还有的与身体融为一色,绿油油的。它的前肢是两把“大刀”,上有一排坚硬的锯齿,末端各有一个钩子,用来钩住猎物。我目睹过螳螂捕食,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扑向蝗虫,用那对“大剪刀”狠命钳住对方。没过多久,蝗虫就一命呜呼了。
早在多年前人们就对螳螂捕食动作进行过细致观察,创造出了著名的螳螂拳。其拳法正迎侧击、虚实相应、长短兼备、刚柔相济、手脚并用,使人难以捉摸,防不胜防;用连环紧扣的手法直逼对方,使敌无喘息机会。由此可见,螳螂是一个真正的“武术家”。
我想,每个人都有印象较为深刻的虫事,像是勤劳勇敢的蜜蜂、叫唤不停的知了、漫天飞舞的蝴蝶、好勇斗狠的蟋蟀、集结成列的蚂蚁、织网吐丝的蜘蛛、毒性极强的蝎子等等。正是有了无数这样的小生灵陪伴在我们身边,让我们的生活多了更多的故事,添了更多的滋味。

山野 汤青 摄
□王月英
终于有机会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老家。
整个村子变得漂亮时尚,整齐划一的白墙蓝瓦的砖房,太阳能路灯笔直地立在水泥道两旁,村小学改建成了休闲广场,连家家户户门前的菜园子都让出一半,变成了停车场。遗憾的是,小时候常见的鸡鸭鹅不见了,路上没有上蹿下跳的淘小子们,更看不到挎着篮子去河边洗衣服的姑娘。
这和我梦中的故乡不一样了。
梦里的故乡屋前屋后有各类蔬菜、果树,有孩子们下河摸鱼上树掏鸟蛋的身影,有在地里锄草的汗水,更有村东头大片塔头甸子里的哈糖果朝我招手。
恍然间又回到了儿时的暑假。村前村后玩腻的我们,总会约着向东,向七八里外的乌苏里江挺进。想去隔江看看对面有没有人家,想去验证一下江边的沙滩是不是金色的。
行走在乡间小路上,其左侧就是一望无际的塔头甸子,现在被称为湿地。塔头上生长着一丛丛灌木。一到夏天,那灌木树丛里的果子就会变紫,果子形如瘦长的灯笼,外面裹着一层白霜,托盘是红色的,摘一颗放嘴里,酸酸甜甜,特别解渴,比曹操的望梅止渴管用得多。我们当地人称它为“哈糖果”,其实人家有大名的,叫蓝莓。
从江边往回返时,碰到哈糖果时会把褂子脱下,两个袖子捆在腰上,扯起后身衣角,兜着摘下来的哈糖果,屁颠屁颠往家跑。回到家后,找一个罐头瓶子,把哈糖果塞进去,放上点白糖,扣上盖,藏到厦子里。过几天取出来吃,那股子酸甜劲至今还留在唇齿间。
当然,有时被染紫的褂子会暴露哈糖果的存在,一顿胖揍是肯定跑不了的。因为大人们绝对禁止我们小孩擅自去塔头甸子的,那里的沼泽地会吃人。
小学毕业那年的暑假,镇上有人高价收哈糖果,说是可以出口,外国人拿去做饮料。我想去挣学费,再三央求下,父亲终于答应带我去草甸子里摘哈糖果。父亲在前面领路,试探着踩那些结实的塔头,以防掉进沼泽地里。有父亲在,就不会有危险。我拎着水桶,穿着水靴子,特别坦然地跟在父亲后面,东张西望地寻找着哈糖果。哈糖果喜欢热闹,遇到就是一大片。桶里的哈糖果越来越多,我的上学梦越做越远。
如今,却再也寻不到塔头甸子,再也摘不到那酸酸甜甜的哈糖果。我暗自思量,如果自己一直在,一直陪伴着哈糖果,是不是结果就不一样呢。其实也未必,只是不同的选择带来不同的失落罢了。

□晴澜
清晨,我下楼去散步。清明时节,空中飘着霏霏细雨,如丝般冰凉光滑,细密地滑过裸露的肌肤,打湿了头发,沾了衣裳。我没有撑伞,也没戴帽子,穿着短衣短裤,任由雨点打在皮肤上。
空气清冽甘甜,还有些淡薄的凉意。黑白灰在天空随意泼洒,变幻成无数的国画,意境深邃,灵动飘逸。空中积压着厚厚的灰色云层,感觉随时会来一场“哗啦啦”的大雨。但是大雨一直未来,是不是因为春风使劲儿吹?吹啊,吹得大树“哗哗”响,吹得满地落英,也吹散了乌云。天空时而明亮,时而乌黑,那是风与云在快乐地游戏、相恋吧?
最喜欢小区的人工湖了。天空时时变幻,湖水随时应和。乌云飘过来时,湖面是灵动的中国画;春风不时撩拨她的心弦,湖水快乐地颤动,荡起阵阵涟漪。
这个时节,最快乐的莫过于花草树木了。如油的春雨滋润着它们,生机勃发。小草上贴附着雨珠,花朵上滚动着雨珠,树上悬挂着雨珠,万物好像都痴迷着雨。新的小草长出来了,毛茸茸的,一小片、一大片伸展开来,温柔、坚定地茂密生长。新叶长出来了,老叶还未脱落,各种层次的绿竞相展示,有浓有淡,或明或暗:浅绿、嫩绿、深绿、暗绿;或者糅杂了其他颜色:青绿、碧绿、黄绿、褐绿,真是绿色主宰的时节。
每个清晨当属鸟儿最快乐,沉寂了一整夜,东方稍亮,它们就欢腾起来,尽情歌唱。处处闻及鸟鸣,清脆尖厉的,温柔浅唱的,还有布谷鸟的声音“李贵娘”,最是特别,婉转悠扬,又似透着无尽的忧伤。小时候,妈妈告诉我一个悲伤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女人名叫李贵娘,因被婆婆嫌弃而投河自尽。其丈夫听到消息后,忧郁悲痛而死,化为布谷鸟,在每一个春天来临时,一遍一遍呼唤她的名字。
转过一处屋角,传来缕缕幽香,绵密又浓烈,只见洁白温润的栀子花挺立枝头。每每看到它们,就会想起逝去30年的外婆,从前在这个季节,经常为我做独特美味的栀子花鸡蛋汤。我闭上双眼,站在树前,浓浓的花香就像外婆的爱,紧紧包绕着我。外婆,那个最爱我的人,如今躺在千里之外的坟茔里。外婆,您的爱一直鼓舞和感染我,我很快乐和感恩。
这是一个雨的时节,绿的时节;也是思念的时节,爱的时节。


□侯淑荷
近日,看到一个令我触动的视频。吉林通化的一位女子,在收拾母亲遗物时,意外发现一个装满银杏叶的信封,打开之后发现,是母亲在父亲去世的十年里,每到父亲忌日那天,她都会去经常与父亲散步的路上,捡一枚银杏叶,然后在银杏叶上写满对父亲的思念。
这些记满思念的银杏叶深深打动了我,也让我的思绪回到公婆生病的那段难忘的时光。公婆身体一直很硬朗,6年前的一天,公公突然感觉身体不适,我们带老人到大医院检查身体,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公公进入医院以后就没能够再出来。
公公是做地质工作的,天南海北地走,婚后与婆婆聚少离多,后来又入伍到了新疆,更是几年也回不了一次家。公公家贫,他少年丧父,又是家中长子,公公离家在外,婆婆要帮助照顾一家老小,还要干繁重的农活,婆婆生四个孩子的时候,公公都不在身边。婆婆吃了很多常人无法想象的苦,却从来不大提这些。
公公住院的日子里,婆婆每日念叨说:“老爷子常年锻炼身体,从来没得过什么大病,体质好,一定会没事的。”又说:“不求他能像原来那样健康,只要能回来,天天看着他,照顾他,给他做饭吃,我就心满意足了。”
记得端午节那天,公公已经病得很重了,家人都在医院陪护公公,我在家陪婆婆过节。清早,我早早出去买回了艾蒿和鲜艳的葫芦,挂在了公婆的房门上,那天婆婆很高兴,一直说:“你这孩子有心,‘葫芦’冲一冲你爸爸病就好了,就能回家了。”
只是,令人遗憾的是,公公在医院的全力抢救之后,还是离开了。
公公离开以后,我们怕婆婆孤单,家里一直留人陪伴着她,和她聊天,劝慰伤心中的她。尽管这样,公公离开不久,婆婆因为思虑过度还是得了重病住进了医院里。幸运的是抢救及时,婆婆在医院调养一段时间以后康复了。
婆婆回到家以后,依旧满眼都是忧伤,公公不在的家,处处都是公公的影子。无论我们怎么开导婆婆,她都郁郁寡欢,常常一个人流泪。转眼到了中秋节,早晨婆婆精神尚好,只是言语间都是对公公的想念。婆婆说:“老爷子一辈子都不会做饭。过节了,他一定很孤单。”说着说着又流下泪来。我们劝慰了好一会,婆婆心情才好些。
和婆婆在阳台上聊了一会天,婆婆说有些累了,我们扶着婆婆回房间休息。爱人开始在厨房准备节日的午餐。不一会,婆婆叫在厨房做饭的爱人说:“儿子,我有些不舒服。”爱人急忙跑到房间一手扶着她坐在床上,一手拨打120。这时,婆婆拉住爱人的手说:“儿子,我不去医院。”谁能想到,这就是婆婆说的最后一句话,疾驰而来的120也没能挽回婆婆的生命。就这样,婆婆离我们而去了,与公公离世只相隔85天。那是一个没有明月的中秋节,让我们这些孩子从此走失了回家的路。
有时候,我们会想,一定是婆婆怕公公一个人过节太冷清了,才舍得抛弃她疼爱的儿女去找公公团聚去了。每次想起公婆,我的心里都充满了思念和感动,思念两位可亲可敬的老人,感动他们淳朴至真的爱情。

□查晶芳
我每次上早读课,在街角等车,总是看见那个老人。他拿着大扫帚,一边忙碌,一边唱歌,声音不大,但很欢快。
第一次见他是在前年深冬的一个早晨。我紧赶慢赶6点25分下了楼,外面还黑漆漆的,一个人影也没有。唉,这么冷的天起这么早,大概只有我们当教师的吧。心里嘀咕着,脚下可不敢怠慢,一路小跑,往街口赶校车。
咦,远远听到前面有人在唱歌。越来越近,听到词了:“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劳动,为她打扮,为她梳妆……”嗓音虽然有些沙哑,但中气还挺足,情感也很投入。这是谁呀?拐过街角,一个橘黄的身影映入眼帘。原来是一名环卫工人,和我一样,也在赶早上班呢。他看上去年近花甲,矮矮瘦瘦的,宽大的工作服套在身上显得空空荡荡,如果把他手中那大扫帚竖起来,估计和他差不多高。他边扫边唱,见我看着他,有点不好意思,停了歌声,对着我微微一笑。我也冲他略一点头,转身上了车。车启动了,橘黄色的身影越来越小,那歌声却好像并未远去。
从那以后,每周上早读课我都能碰到他。时间一长,我们成熟人了。每次,他依然是挥着扫帚,哼着歌,唱得最多的就是《在希望的田野上》。有时,他看见我在跑,就会暂停歌声,对着我喊:“车还没走,不要急的哦。”看我气喘吁吁地站定,他便露出慈祥的笑容。有一次他还说:“你们当老师的不容易,要起这么早,还天天要费心费神,现在的小鬼不好教呢。”我说他也辛苦,他连连摆手:“我只要把地扫干净了,心里就亮堂了,不烦其他神呢。”他弓下身子,背着双手,眼睛盯着扫过的地面,慢慢巡视一圈。像指甲大的碎纸片、寸许长的细棍子等这些“漏网之鱼”全逃不过他的法眼,将它们“就地正法”后,他才哼着歌坐下歇会儿。
有一次,我忍不住说:“您唱得挺好的呀。”见我夸他,他很意外,略显羞涩:“我瞎唱唱呢。”嘴里谦虚着,满脸的皱纹却笑出了深沟。我问他咋这么喜欢唱这首歌。“这歌好。唱的就是我们农村的事,田埂、小河、麦子、高粱、插秧,还撒网打鱼,我一唱做事更有劲。”老人笑咪咪地絮叨着,我也忍不住笑了。
一天早晨,我正准备上车,看到一名匆匆忙忙的路人在马路正中弄翻了拎在手里的早点,面条和着汤水洒了一地。那人跺脚嘟囔着:“唉,大清早把饭泼了。”蹲下身准备收拾。当时,老人刚扫完地坐着休息,快步走过去说:“我来搞,你忙你的去。”那人连声说抱歉,老人摆摆手:“麻烦个啥,本来就是我应当做的事。”
我原以为老人这么大年纪还做环卫工人,不是经济困窘就是儿女不孝。那天校车晚点了,我和老人聊了一会儿家常,得知他的两个儿子在城里“混得都蛮好”,对他也关心照顾得很,早就不同意老父亲做这份工作了,但老人自己执意要做。“这事情做习惯了,不做还真难受。也怪,我歇在家里总是这痛那痒的,后来知道这路段缺人,就来了。你别说,一做事那些毛病全都好了。”老人看着马路的眼神满是喜悦,像对着自己的孩子般深情。
“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人们在明媚的阳光下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变样……”老人又欢快地唱起来了。
□张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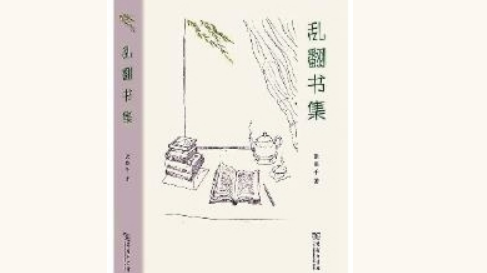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