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子龙 1941年生于河北省沧州,曾任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多次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奖。代表作有《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农民帝国》等。201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14卷本《蒋子龙文集》。


古往今来圣哲们的终极追问,无非是“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表现了现代地球人对历史与文化的焦渴,或者还有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忧虑。没有历史文化的留存,就没有人类生存的记忆和痕迹,人类的存在将成为一片虚无。
法国哲学家亚兰说:人类史就是宗教的历史。所以,人们至今来澳门古城区,常常觉得“一座庙连着一座庙,一个教堂接着一个教堂”……澳门开埠建城,其“历史城区”以鲜活的生命力,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独特的一页。15世纪后期,葡萄牙成为海上强国,想用舰队打通中国贸易市场,在浙江、福建、广州……屡战屡败,处处碰壁。几十名溃逃的散兵,冥冥之中受中国民间宗教的指引,在妈阁庙前的海滩上岸,所以葡萄牙人最早称澳门为“妈阁”。当时的澳门小岛上,只有400多人,精神上仰仗着妈祖的慈护。
1578年,意大利籍的耶稣会传教士范礼安初登澳门,发现这是块宝地。此后30年间,他六次来澳门,并到处公开宣讲:“中国是个秩序井然的高贵而伟大的国家,相信这样一个有智慧而勤劳的民族,决不会将懂得其语言和文化、并有教养的耶稣会传教士拒之门外的……”这是他的真情实感,并不是虚情假意的恭维,因为他无须如此。当时他是“果阿至日本的东印度区耶稣会视察员”,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话,他成为西方宗教在澳门的奠基人,创建“耶稣兄弟会”,并指定意大利天主教教士利玛窦为“中国传教团主管”。
利玛窦抵达澳门后,“操汉语,着华服,刻苦研究中国典籍,讲授西方的天文地理历算之学,将天主教汉化”。他在尊重中国文化的前提下,取长补短。他通晓六经子史,并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本国出版,开西方人译述中国经典的先河。他还首创用拉丁字母注汉字语音,成为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创始人。同时以西洋科学知识、天文仪器作为传教的手段,他刻印世界地图时,名为《坤舆万国全图》,呈献给明神宗,让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有五大洲,以及中国真实面积到底有多大的真相。利玛窦还以口授的方式由徐光启笔译了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
人类发展史的本质是思想史,在主管思想的宗教及文化的“四梁八柱”确立之后,澳门的社会结构开始形成,在开埠300多年的时间里,来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意大利、日本、瑞典、英国、法国及非洲等不同地区的人,他们在澳门的古城区内盖房子、修马路……通过各类社会及文化活动,开展多姿多采的生活。
——这就是澳门的“历史城区”,也可以说是“世界的历史城区”。因得风气之先,澳门也成了“中国境内接触近代西方器物与文化最早、最多、最重要的地方”,创造了诸多的“中国第一”:
1594年建成的圣保禄学院,成为整个远东地区最早的一所西式大学,清代著名画家常州吴渔山,便是第一个就读于此院的留学生;第一家西式医院——白马行医院;第一座西式剧院——岗顶剧院,既上演西方歌剧,后来又可上演中国古典名剧《牡丹亭》;第一座现代灯塔;第一份外文报纸……
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大三巴牌坊”。原是圣保禄教堂的前壁,1835年一场大火,烧毁了整座宏大坚固的教堂,却独留一面门脸墙,孑然而立。看似极单薄,实质却无比强固,近200年来任台风暴雨、雷电交加,它始终纹丝不动,历经岁月沧桑的洗礼,竟然成了澳门的标志。
——飘逸而凝重,肃气又从容。
它像历史的骨骼。赤裸裸却明媚绝伦,气象清扬。每天都有无以计数的人向它致敬,用想象还原了它丰满的血肉。它在隐逸中静观世事,表达了一种最深刻的历史和人生经验。
鉴于此,澳门“历史城区”有两个特点,或许是《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独一无二的:其一,它不是一个单项的文化遗迹,而是一片老城区,大街小巷,楼阁亭台……对比之下,当你登高俯瞰一片片崭新的楼群时,会感到它缺点什么,缺时间的凝练,缺历史的沉淀,缺文化的品位……总之,缺少灵魂。
其二,澳门“历史城区”不是一个历史片段,不是白天人头攒动,夜晚一片死寂的供游人参观的胜地,而是代表了完整的澳门历史和现实。这里依然人烟稠密,车水马龙,他们不是匆匆过客,他们是历史的主人,也是生活的主人。历史滋养着他们的精神,也深入到他们日常生活琐细的纹理之中,甚至可以说他们就生活在历史中。
法国思想家布罗代尔这样认识历史:“像大海深处那样沉默而无边无际的历史内部背后,才是进步的本质,真正传统的本质。”民气充盈,老百姓的生生不息,才是历史的血脉,构成文化的永恒。文化以及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不是花里胡哨的东西,一定是与生存结构相匹配的。
文化是一种口碑。因此,澳门有一种文化上的自信。
中国文化有两个传统:以史为鉴,以天为则。何为天?“王者以百姓为天”。澳门“历史城区”的历史中,以独有的悲情与欢乐、屈辱与暴烈……在时空绵延中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澳门人,自然而然地有了精神的认同、历史的认同,有了共同的文化自觉,使古城区里氤氲着一种温润宽和的气韵。
澳门是历史的馈赠。其“历史城区”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证明澳门民智很高。人文环境就是文化。这就使这个城区,既是历史城区,又是现实城区。从内涵到外表,极其协调一致,深厚雄盛,异彩荡漾。澳门“历史城区”仿佛时光隧道,在这里可以自由行走在历史中,又可从历史中不知不觉回到现实。历史在现实中是活的,现实又了无痕迹地接续着历史。
历史既是一种明确的经验,历史里又藏着未来的密码,现代澳门人的解读正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而“历史不过是文化史”。不是澳门以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荣,而是“世界文化遗产”中为有澳门“历史城区”,感到庆幸。
古城厚文,名重千秋,是为不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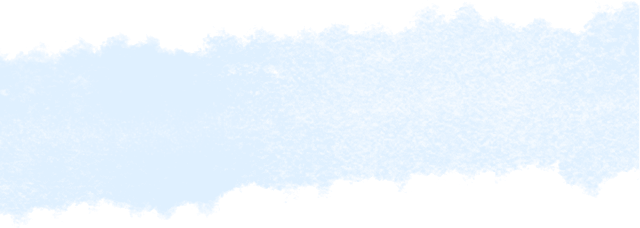



蒋子龙 1941年生于河北省沧州,曾任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多次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奖。代表作有《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农民帝国》等。201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14卷本《蒋子龙文集》。


古往今来圣哲们的终极追问,无非是“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表现了现代地球人对历史与文化的焦渴,或者还有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忧虑。没有历史文化的留存,就没有人类生存的记忆和痕迹,人类的存在将成为一片虚无。
法国哲学家亚兰说:人类史就是宗教的历史。所以,人们至今来澳门古城区,常常觉得“一座庙连着一座庙,一个教堂接着一个教堂”……澳门开埠建城,其“历史城区”以鲜活的生命力,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独特的一页。15世纪后期,葡萄牙成为海上强国,想用舰队打通中国贸易市场,在浙江、福建、广州……屡战屡败,处处碰壁。几十名溃逃的散兵,冥冥之中受中国民间宗教的指引,在妈阁庙前的海滩上岸,所以葡萄牙人最早称澳门为“妈阁”。当时的澳门小岛上,只有400多人,精神上仰仗着妈祖的慈护。
1578年,意大利籍的耶稣会传教士范礼安初登澳门,发现这是块宝地。此后30年间,他六次来澳门,并到处公开宣讲:“中国是个秩序井然的高贵而伟大的国家,相信这样一个有智慧而勤劳的民族,决不会将懂得其语言和文化、并有教养的耶稣会传教士拒之门外的……”这是他的真情实感,并不是虚情假意的恭维,因为他无须如此。当时他是“果阿至日本的东印度区耶稣会视察员”,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话,他成为西方宗教在澳门的奠基人,创建“耶稣兄弟会”,并指定意大利天主教教士利玛窦为“中国传教团主管”。
利玛窦抵达澳门后,“操汉语,着华服,刻苦研究中国典籍,讲授西方的天文地理历算之学,将天主教汉化”。他在尊重中国文化的前提下,取长补短。他通晓六经子史,并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本国出版,开西方人译述中国经典的先河。他还首创用拉丁字母注汉字语音,成为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创始人。同时以西洋科学知识、天文仪器作为传教的手段,他刻印世界地图时,名为《坤舆万国全图》,呈献给明神宗,让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有五大洲,以及中国真实面积到底有多大的真相。利玛窦还以口授的方式由徐光启笔译了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
人类发展史的本质是思想史,在主管思想的宗教及文化的“四梁八柱”确立之后,澳门的社会结构开始形成,在开埠300多年的时间里,来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意大利、日本、瑞典、英国、法国及非洲等不同地区的人,他们在澳门的古城区内盖房子、修马路……通过各类社会及文化活动,开展多姿多采的生活。
——这就是澳门的“历史城区”,也可以说是“世界的历史城区”。因得风气之先,澳门也成了“中国境内接触近代西方器物与文化最早、最多、最重要的地方”,创造了诸多的“中国第一”:
1594年建成的圣保禄学院,成为整个远东地区最早的一所西式大学,清代著名画家常州吴渔山,便是第一个就读于此院的留学生;第一家西式医院——白马行医院;第一座西式剧院——岗顶剧院,既上演西方歌剧,后来又可上演中国古典名剧《牡丹亭》;第一座现代灯塔;第一份外文报纸……
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大三巴牌坊”。原是圣保禄教堂的前壁,1835年一场大火,烧毁了整座宏大坚固的教堂,却独留一面门脸墙,孑然而立。看似极单薄,实质却无比强固,近200年来任台风暴雨、雷电交加,它始终纹丝不动,历经岁月沧桑的洗礼,竟然成了澳门的标志。
——飘逸而凝重,肃气又从容。
它像历史的骨骼。赤裸裸却明媚绝伦,气象清扬。每天都有无以计数的人向它致敬,用想象还原了它丰满的血肉。它在隐逸中静观世事,表达了一种最深刻的历史和人生经验。
鉴于此,澳门“历史城区”有两个特点,或许是《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独一无二的:其一,它不是一个单项的文化遗迹,而是一片老城区,大街小巷,楼阁亭台……对比之下,当你登高俯瞰一片片崭新的楼群时,会感到它缺点什么,缺时间的凝练,缺历史的沉淀,缺文化的品位……总之,缺少灵魂。
其二,澳门“历史城区”不是一个历史片段,不是白天人头攒动,夜晚一片死寂的供游人参观的胜地,而是代表了完整的澳门历史和现实。这里依然人烟稠密,车水马龙,他们不是匆匆过客,他们是历史的主人,也是生活的主人。历史滋养着他们的精神,也深入到他们日常生活琐细的纹理之中,甚至可以说他们就生活在历史中。
法国思想家布罗代尔这样认识历史:“像大海深处那样沉默而无边无际的历史内部背后,才是进步的本质,真正传统的本质。”民气充盈,老百姓的生生不息,才是历史的血脉,构成文化的永恒。文化以及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不是花里胡哨的东西,一定是与生存结构相匹配的。
文化是一种口碑。因此,澳门有一种文化上的自信。
中国文化有两个传统:以史为鉴,以天为则。何为天?“王者以百姓为天”。澳门“历史城区”的历史中,以独有的悲情与欢乐、屈辱与暴烈……在时空绵延中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澳门人,自然而然地有了精神的认同、历史的认同,有了共同的文化自觉,使古城区里氤氲着一种温润宽和的气韵。
澳门是历史的馈赠。其“历史城区”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证明澳门民智很高。人文环境就是文化。这就使这个城区,既是历史城区,又是现实城区。从内涵到外表,极其协调一致,深厚雄盛,异彩荡漾。澳门“历史城区”仿佛时光隧道,在这里可以自由行走在历史中,又可从历史中不知不觉回到现实。历史在现实中是活的,现实又了无痕迹地接续着历史。
历史既是一种明确的经验,历史里又藏着未来的密码,现代澳门人的解读正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而“历史不过是文化史”。不是澳门以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荣,而是“世界文化遗产”中为有澳门“历史城区”,感到庆幸。
古城厚文,名重千秋,是为不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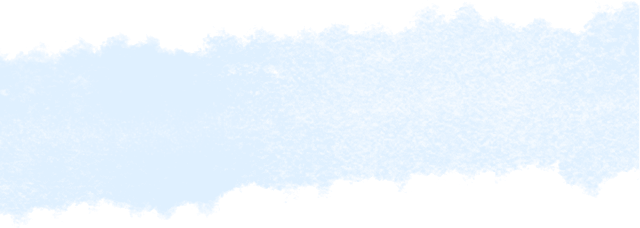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