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心安处是吾乡
——品读长篇小说《宝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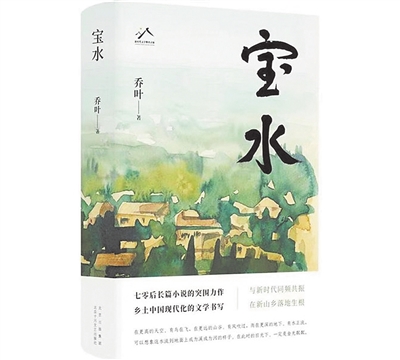
□ 王雅芬
乔叶的长篇小说《宝水》用温润诗意的笔触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新时代乡村建设的故事。宝水村“人在人里,水在水里”,谁也离不开谁。各色村民、乡建专家、基层干部、返乡青年、支教大学生纷纷热情加入乡村建设的队伍,同心合力将太行山深处的这个传统山村建设成为独具特色的文旅小镇。宝水村迎来了新一轮的春夏秋冬,在四时节序不变的风俗文化中人情似锯,你来我往,焕发生机。极具乡土气息的人情事理,在琐碎而鲜活的乡村生活中散发出新的光彩,治愈人心。
主人公地青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闯入宝水村的。她有着和她名字一样割裂的情感。青萍从小跟着奶奶在故乡福田庄长大,奶奶和叔叔的宠溺造就了她对故乡和土地的深厚感情。她爱故乡,爱那一段被叔叔放在肩膀去够榆树、够槐花、够柿子的童年时光。她像一株浮萍一样,顺着时光的水流远离故乡后,又觉得故乡的人情似锯,锯得她生疼。村里人简单的寒暄拉家常,她觉得尴尬;奶奶让父亲一件件给村里人办事,她心生厌恶;奶奶列举当年村里人帮忙的小事,教她要感恩,她拒绝无原则的宽容和忍耐……最终,当父亲为人情死于一场车祸后,青萍对故乡的人情事理从无奈、尴尬、沮丧变为痛恨。随着奶奶和丈夫的去世,她甚至不愿意再靠近福田庄这个伤心地。
这种不自知的割裂让青萍长期失眠。后来,她发现在乡下能睡好,于是趁着好友老原回老家开民宿的契机来到了离故乡福田庄不远的宝水村。在这里,她先是若即若离地旁观,继而被红红火火的乡村振兴建设队伍吸引并加入,在帮忙照看老原新开的民宿之外,被动担任起村史馆的筹建工作。在深度参与宝水村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她看到了村民们敲瓷砖、搞卫生,翻新老宅做民宿的热情,也看到村民乱收停车费,几根香椿芽便敢索要五百块的自私。她看到了基层干部大英的泼辣善良,大事明、小事清,大公无私为宝水,也看到了大英为女儿娇娇的私心,看到了大英处理乡村事理的难处。她看到了返乡青年鹏程和雪梅的能干和恩爱,也看到了七成家暴秀梅,秀梅隐忍伺机反抗成功的辛酸。她看到乡村建设专家孟胡子的赤诚和专业,也看到民宿老板老原的生意经和坚守原则。她看到支教大学生肖睿和周宁辅导留守儿童文化课的温馨,也看到在乡村普及性教育所遇到的巨大阻力。
青萍开始重新理解乡村。在宝水村村民从容而恬静的日子里,她的失眠症被治愈了。最后,青萍在九奶的喜丧中完全认同了乡村朴素厚道的人情事理,也终于和那个怨恨自己的过去和解,牵手老原,成为真正的宝水人。
所以,什么是老家?老家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在世的老人在那里生活,等着我们回去。去世的老人在那里安息,等着我们回去。乡村,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处心灵的归宿。那片土地,那个村庄,那座房子,那些亲人,就是故乡,就那样待在原地,等着我们回去。
直面孤独 不负人生
——读《一句顶一万句》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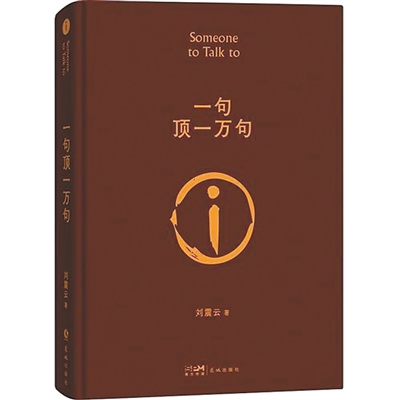
□ 黄伟兴
作家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成熟大气、叙事直接的小说,它展现了底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普通人的“追寻难”和“百事哀”,深入洞察书中人物内心深处所隐藏的孤独和无力感。
从书名来看,人心里的孤独源自人与人之间的“说得着”和“说不着”,“说得着”时一句话顶一万句,“说不着”时一万句都是瞎话。在阅读全书的过程中,读者会不自禁被作者智慧又凝练的句子触动。书中的人物身份背景不相同,却有着十分相似的心路历程。小说的前半部分写的是往事,后半部分写的是当下,分别对应着杨百顺和牛爱国,两人都为摆脱心中的孤独而远走他乡。
细细品读《一句顶一万句》会发现,杨百顺和牛爱国这两个人物角色辗转奔波了多个地方,几乎跑遍了中原地区,他们似乎不曾停歇,永远在路上。杨百顺与父亲、兄弟都“说不着”,他换了许多份工作,改了很多个名字;牛爱国与妻子“说不着”,他服完兵役归来后,因婚姻生活不顺意而到处找人出主意。他们在路上经历了各种事情,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人,心里的犹豫慢慢散去。这与很多人的生活状态如出一辙,一旦有闲暇时间就开始胡思乱想,总是担心“闲出病来”。无论是年纪大了还是退休了,我们总喜欢寻找事情来做,原因都是一样的。表面上看是在寻找事情来做,实际上却是希望通过忙碌来缓解内心的孤独感。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人物是一面镜子,也是一种符号,是与读者自己“对话”的一面镜子,杨百顺不断地“试错”换工作,剃头、杀猪、染布、破竹子以及种菜卖馒头,工作从百般挑剔变成了糊口即可;牛爱国经受了婚姻和情感的多重打击,到最后释然。他们的一生不断地被生活打击着,内心也在变化着,却从未放弃过抗争。他们所经历的,其实是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在牛爱国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的母亲曹青娥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这一句话在书中出现过两次,是本书的点睛之笔。它清晰地告诉我们,世事难料,没有办法选择的时候,便要坦然去接受与面对;无论以前的日子怎么样,都要过好后面的日子,过去无法改变,将来才值得我们去期待。我们要在短暂又漫长的一生中,找到那个“说得着”的人,让灵魂诗意地栖息。
刘震云的作品语言简洁、接地气,他用那份温情与细腻,为书中人物破碎的心进行缝补,与读者“一诉衷肠”,人害怕孤独,所以说话,但人无法脱离孤独,因为旧日子永远都在,使你摇摆在孤独和不孤独之间。《一句顶一万句》让我们在孤独中仍能感受到生命中的执着与顽强,找回对生活、对世界的热爱,直面孤独,不负人生。
故乡拨动你我的心弦
——《也傍桑阴书华年》里的精神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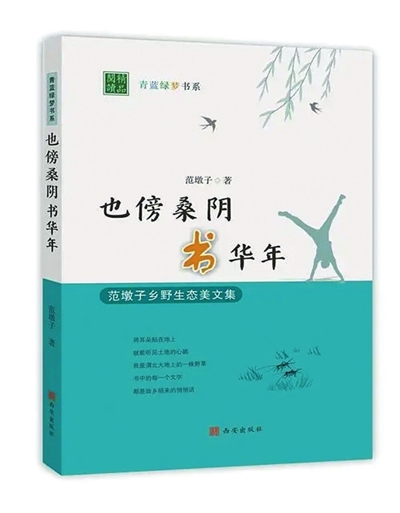
□ 鹿 离
对很多作家来说,故乡是永不枯竭的灵感之源,童年则是他们写作道路的起始点。作家范墩子的散文集《也傍桑阴书华年》延续其一贯灵动、质朴、诗意的语言风格,这一次他的情感流淌不再拘束、收敛,自然地捡拾其散落在山间草木上的童年音符,编织成一首献给故乡渭北大地的歌谣,悄悄撩拨你我记忆深处的心弦。
文学与故乡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当谈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时,范墩子如是说:“我是一个随时把童年记忆和故乡记忆携带在身上的人。”从短篇小说集《我从未见过麻雀》以孩童视角构筑新时代中国少年的“心灵史”,长篇小说《抒情时代》以“我”的视角讲述小镇少年从故乡走进城市的成长史,到儿童小说《去贝加尔》以成人视角描绘勇敢少年寻找希望与爱的故事,到如今的散文集《也傍桑阴书华年》从回望视角记录行走于故乡的所见所悟,即便范墩子自陈“已成为了故乡的局外人”,但他的写作从未离开童年和故乡,笔下常常出现麻雀、豹榆树、桑柘、牧羊人、唐陵遗迹等这些带有明显故乡标志的物事,字里行间处处藏着故乡的风物地理人情,故乡是他不可缺失的精神家园。
文学是故乡映在心田的影子,也是寄托深情的信仰。尽管他已走出乡村,到大城市扎根生活,可他的内心深处却迷恋着宁静淳朴的乡野生活,苍凉的大地、寂寥的山风、草木的微笑、河流的嗓音……当他将耳朵贴在地上,就能听见土地的心跳,而当他的心贴在地上,“我那遗失的睡梦就重新苏醒了过来,活了过来”。于他而言,只有将自己投入渭北大地的怀抱,细细回望和描摹故乡的风物人情,他的身心才能得到真正的放松。他在后记《从故乡出发的写作》中写道,“故乡是逼仄的,更是辽阔的”。童年时代的故乡风景,成为他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也成为他最初也是最成功的表现天地。他也说,“我是渭北土地上的一株野草”,将宁静山风中故乡捎来的悄悄话,写成审视故土过往和当下时代的文字,越写越朴素,越写越宽广。
每个人都有一片文学的故乡。范墩子对故乡满怀深情,一次又一次走在回乡的路途上,走进山间田野重温故乡的风土人情,也在行走中正视自己内心深处的复杂图景。从家乡出发的写作是一种精神还乡,也是一次次的精神回归之旅。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故乡的深深眷恋,直陈自己喜欢靠在豹榆树厚实的树身上,任斑驳的树影唤醒童年的记忆,感叹“每次看到贫瘠的塄坎上却长着许多开着花的小雏菊,我的心里都会涌出无限的感动”,他早已摆脱地理上的“狭隘的故乡概念”,可故乡依旧是他无法割舍的情结,无论是故乡黑暗的地方,还是故乡光明的地方。“童年是我写作的富矿”,书中收录多篇追忆童年往事的文章,文笔优美,情感质朴,但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滚铁环》一文,篇幅虽短,却令人感到亲切温暖,铁环也曾滚过我的童年时光,我也曾写过类似的文章。故乡的童年记忆有苦有甜,可当我们身在远方对家乡和童年深情凝眸时,内心深处的小天地总是充满温馨,不安的情绪得以慢慢平息,温暖溢满心头。故乡本是一个苦涩与美好共存的话题,他直面自我的故乡叙述中却鲜少苦涩的味道,更多的是纯净的美好。细细究之,他并非无视故乡的逼仄和荒凉,也不缺少审视的目光和勇气,而是在“一边厌倦着城市生活,又无法摆脱得开城市生活”的心理纠缠中,童年故乡的记忆成了他精神的栖息地,哪怕是苦涩的记忆也成为一种美好。
正如范墩子所言,我们已“很难再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返乡”,这是生活的无奈,也是自然的规律。故乡总是在不经意间拨动你我的心弦,当我们感到疲惫和孤单的时候,不妨多回家看看,望望归乡的路,哪怕只有一瞥,哪怕只是纸上故乡,都能感到母亲怀抱般的放松和温暖。
□ 张斯
“书读完了”,我盯着封面上这几个大字,生出些许困惑:古今中外,典籍如浩瀚宇宙之星辰,究竟是什么人敢口出狂言?我移目到署名处,金克木,困惑消散了多半。他以小学学历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传奇经历为大家所熟知。但学贯中西的金克木先生“宣称”书读完了,似乎与他一贯求知若渴、谦虚谨慎的治学理念背道而驰。然而我心中又升腾出希望,读完此书,是不是也能掌握些能将书读完的技巧。
金克木先生提出了“书可以读完”的依据:“把书读完”首先是要读什么书,每一种文化都有几部最重要的文献经典,它们既不依附于其他书,又是整个系统的知识基础,把中外文化中的这类书通读之后,就可以说是“书读完了”。他列出根源性典籍,以中国为例,他认为不读《周易》《诗经》《尚书》《左传》《礼记》《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就无法读韩愈、朱熹的书,就连《西厢记》《红楼梦》中的词句用典也无法体会。他还分享了几种读书方法:把作者、书籍当成朋友,谈论式、质疑式的福尔摩斯读书法;读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读书空白内容,思考文字弦外之音的读书得间法;读书、读人、读物的方法。
《读书·读人·读物》中道:“一本书若满是字,岂不是一片油墨?没有空白是不行的,像下围棋一样。古人、外国人、现代人作书,好像是都不会把话说完、说尽的,不是说他们‘惜墨如金’,而是说他们无论有意无意都说不尽要说的话。越是啰嗦废话多,越说明他有话说不出或是还没有说出来。那只说几句话的就更是话里有话了。”要想读懂书中的真意,不光要看说了什么,更要看什么没说。有人认为,“当于无字处求之”的读书方法,有过度解读之嫌。但文学创作中,追求言外之意是中国文化的独特精神。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隐秀”的创作理念,被现代国学大师黄侃冠之“文苑最要”。简单来说,隐是字面意义之外的内容,秀是作品中出类拔萃的句子。一部作品如果不包含意蕴丰富的韵味、悠远隽永的意趣、触类旁通的情感,就不能被称为佳作,而以上都只能通过有限的言辞以及言辞之外的空白来营造。要想准确掌握优秀作品中的言外之旨,就需要如金克木先生所说,要将蕴含文明根源性的典籍通读熟读,带着问题与作者对话。
贾岛与韩愈在“推敲”上反复斟酌,这是创作者对言外之意能否准确传达的琢磨。读者若是知晓贾岛曾落魄出家,却又想建功立业的心路历程,就能更好地体会到“僧敲月下门”的克己复礼和目盼心思。在书中所占篇幅不多的“风月宝鉴”为何能成为《红楼梦》的别称?只有体会书中风月宝鉴正面红粉佳人、背面骷髅恶鬼的含义,结合中国传统“正衣冠、知兴替、明得失、辟不祥、驱邪恶”的镜文化,方能体会到深隐在人物背后的尔虞我诈、四大家族的处心积虑,乃至时代的困顿无力。
书读完了,我只掌握了九牛一毛,但也受益匪浅。我穷极一生,也无法达到金克木先生的境界,只能在有限的时间用学到的方法竭尽所能地读懂书,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
书,读不完;读懂,也是妙事。
□ 黄 泰
《繁花》改编自作家金宇澄的同名小说,由王家卫导演,胡歌、马伊琍、游本昌、唐嫣、辛芷蕾、郑恺等主演。全剧聚焦20世纪90年代初以阿宝为代表的普通人在沪上风云际会的生意场中追逐机遇,努力改变自我的成长故事。
在风云变幻的资本市场、复杂的人性、微妙的情感等元素的交织下,《繁花》展现出了极具历史激情和现实感染力的故事,深深地吸引着观众的心。这部剧凭借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和深刻的主题,为观众带来了深刻而真实的震撼,让人深受感动。
进入电视剧《繁花》的世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精致的视觉美感。导演王家卫善于用色彩来衬托故事,借此铺陈演员与故事间的情调。剧中的影像充满了希望和生机,当中不乏对寻常生活、市井姿态的书写:进贤路的拥挤与热闹,华灯初上的黄河路等,带观众细细品味迷离光影下的上海。高度的影像还原,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切身感受到上海的繁华和活力。
在剧中,游本昌扮演的爷叔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纽约的帝国大厦晓得吧,从底下跑到屋顶要一个钟头,从屋顶跳下来,只要八点八秒。”这句话暗示了生意场的残酷现实,凸显他作为阿宝的合伙人所具备的深思远虑和长远目光,也显示出老一代上海人对年轻一代的独特栽培方式与期望。关于阿宝,对他而言最具代表性的词便是“不响”。他说:“做生意,首先要学会两个字:不响。不知道的,说不清楚的,没想好、没规划的,为难自己、为难别人的,都不响。”“不响”,在《繁花》原著出现过多次,它意味悠长,犹如一种沉默的留白。王家卫说:“是什么让阿宝成为宝总,一夜之间成为时代弄潮儿,书里没有体现,我们可以‘补白’。”阿宝有着盖茨比般的派头,他成功过,也失败过,总是激情澎湃且充满信心,有着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和希望。他同千千万万个在上海奋斗的人一样,起起落落,亦如繁花一样花开花落。
剧中对玲子、汪小姐、李李等女性人物角色的表现是一大亮点。玲子嘴硬心软、精打细算,王小姐开朗动人、倔强坚定,李李雷厉风行、智慧干练。用原著《繁华》的句子形容最为令人动容:“一个女人,越是笑容满面,欢天喜地,一翻底牌,越是苦,一肚皮苦水。”除了聚焦这些抢眼的人物外,导演还精心刻画了配角群像,比如冷静的金科、心比天高的小江西,以及脚踏实地、善解人意的露丝。她们身处不同的社会阶层,可她们代表着时代浪潮中在沪奋斗女性不同的外在与智慧,也呈现出她们各具特色的魅力与生命力,让上海这座城市更加鲜活和真实。
在该剧的创作过程中,导演王家卫并非单纯地照搬原著,而是通过自己的独有的方式还原了《繁花》的气质和灵魂,让原著中的阿宝等人物活了起来,增强了故事性并重新处理了叙事节奏,让电视剧和文学互相借力,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电视剧《繁花》从光影到叙事都不乏王家卫式的浪漫维度与格调,他用自己的方式与原著默契配合,让剧中的人物发光发亮,充实了《繁花》的灵与肉。全剧让我们品味到浓郁的上海文化历史韵味和群体奋斗的精神风貌,为我们呈现了一场充满沪上烟火气息的视觉盛宴。
□ 孙功俊
墙上挂着一把锄,身影逐渐斑驳,诸多的陈年往事锈进了岁月里。
所有的经过都有记忆,一把锄也不例外。
那些锄过的杂草,锈进曾经的梦里;那些大豆、花生、芝麻、红薯经过的夏天,锈进远处的风景;那些春天飞起的柳丝,锈进旧时的斑斓。
父亲已经走远,荷锄人无法从时空中返回。
挂在墙上的一把锄,只能木然地看着自己的锈迹斑斑。


此心安处是吾乡
——品读长篇小说《宝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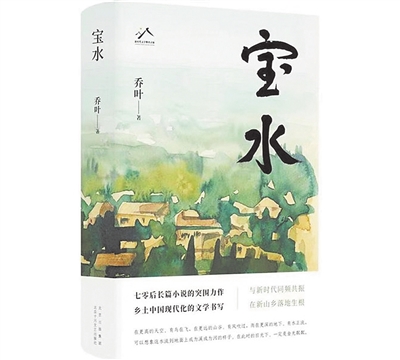
□ 王雅芬
乔叶的长篇小说《宝水》用温润诗意的笔触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新时代乡村建设的故事。宝水村“人在人里,水在水里”,谁也离不开谁。各色村民、乡建专家、基层干部、返乡青年、支教大学生纷纷热情加入乡村建设的队伍,同心合力将太行山深处的这个传统山村建设成为独具特色的文旅小镇。宝水村迎来了新一轮的春夏秋冬,在四时节序不变的风俗文化中人情似锯,你来我往,焕发生机。极具乡土气息的人情事理,在琐碎而鲜活的乡村生活中散发出新的光彩,治愈人心。
主人公地青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闯入宝水村的。她有着和她名字一样割裂的情感。青萍从小跟着奶奶在故乡福田庄长大,奶奶和叔叔的宠溺造就了她对故乡和土地的深厚感情。她爱故乡,爱那一段被叔叔放在肩膀去够榆树、够槐花、够柿子的童年时光。她像一株浮萍一样,顺着时光的水流远离故乡后,又觉得故乡的人情似锯,锯得她生疼。村里人简单的寒暄拉家常,她觉得尴尬;奶奶让父亲一件件给村里人办事,她心生厌恶;奶奶列举当年村里人帮忙的小事,教她要感恩,她拒绝无原则的宽容和忍耐……最终,当父亲为人情死于一场车祸后,青萍对故乡的人情事理从无奈、尴尬、沮丧变为痛恨。随着奶奶和丈夫的去世,她甚至不愿意再靠近福田庄这个伤心地。
这种不自知的割裂让青萍长期失眠。后来,她发现在乡下能睡好,于是趁着好友老原回老家开民宿的契机来到了离故乡福田庄不远的宝水村。在这里,她先是若即若离地旁观,继而被红红火火的乡村振兴建设队伍吸引并加入,在帮忙照看老原新开的民宿之外,被动担任起村史馆的筹建工作。在深度参与宝水村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她看到了村民们敲瓷砖、搞卫生,翻新老宅做民宿的热情,也看到村民乱收停车费,几根香椿芽便敢索要五百块的自私。她看到了基层干部大英的泼辣善良,大事明、小事清,大公无私为宝水,也看到了大英为女儿娇娇的私心,看到了大英处理乡村事理的难处。她看到了返乡青年鹏程和雪梅的能干和恩爱,也看到了七成家暴秀梅,秀梅隐忍伺机反抗成功的辛酸。她看到乡村建设专家孟胡子的赤诚和专业,也看到民宿老板老原的生意经和坚守原则。她看到支教大学生肖睿和周宁辅导留守儿童文化课的温馨,也看到在乡村普及性教育所遇到的巨大阻力。
青萍开始重新理解乡村。在宝水村村民从容而恬静的日子里,她的失眠症被治愈了。最后,青萍在九奶的喜丧中完全认同了乡村朴素厚道的人情事理,也终于和那个怨恨自己的过去和解,牵手老原,成为真正的宝水人。
所以,什么是老家?老家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在世的老人在那里生活,等着我们回去。去世的老人在那里安息,等着我们回去。乡村,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处心灵的归宿。那片土地,那个村庄,那座房子,那些亲人,就是故乡,就那样待在原地,等着我们回去。
直面孤独 不负人生
——读《一句顶一万句》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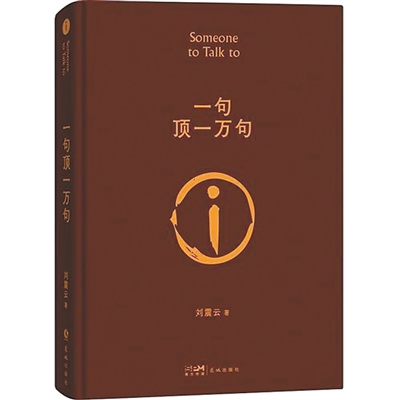
□ 黄伟兴
作家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成熟大气、叙事直接的小说,它展现了底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普通人的“追寻难”和“百事哀”,深入洞察书中人物内心深处所隐藏的孤独和无力感。
从书名来看,人心里的孤独源自人与人之间的“说得着”和“说不着”,“说得着”时一句话顶一万句,“说不着”时一万句都是瞎话。在阅读全书的过程中,读者会不自禁被作者智慧又凝练的句子触动。书中的人物身份背景不相同,却有着十分相似的心路历程。小说的前半部分写的是往事,后半部分写的是当下,分别对应着杨百顺和牛爱国,两人都为摆脱心中的孤独而远走他乡。
细细品读《一句顶一万句》会发现,杨百顺和牛爱国这两个人物角色辗转奔波了多个地方,几乎跑遍了中原地区,他们似乎不曾停歇,永远在路上。杨百顺与父亲、兄弟都“说不着”,他换了许多份工作,改了很多个名字;牛爱国与妻子“说不着”,他服完兵役归来后,因婚姻生活不顺意而到处找人出主意。他们在路上经历了各种事情,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人,心里的犹豫慢慢散去。这与很多人的生活状态如出一辙,一旦有闲暇时间就开始胡思乱想,总是担心“闲出病来”。无论是年纪大了还是退休了,我们总喜欢寻找事情来做,原因都是一样的。表面上看是在寻找事情来做,实际上却是希望通过忙碌来缓解内心的孤独感。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人物是一面镜子,也是一种符号,是与读者自己“对话”的一面镜子,杨百顺不断地“试错”换工作,剃头、杀猪、染布、破竹子以及种菜卖馒头,工作从百般挑剔变成了糊口即可;牛爱国经受了婚姻和情感的多重打击,到最后释然。他们的一生不断地被生活打击着,内心也在变化着,却从未放弃过抗争。他们所经历的,其实是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在牛爱国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的母亲曹青娥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这一句话在书中出现过两次,是本书的点睛之笔。它清晰地告诉我们,世事难料,没有办法选择的时候,便要坦然去接受与面对;无论以前的日子怎么样,都要过好后面的日子,过去无法改变,将来才值得我们去期待。我们要在短暂又漫长的一生中,找到那个“说得着”的人,让灵魂诗意地栖息。
刘震云的作品语言简洁、接地气,他用那份温情与细腻,为书中人物破碎的心进行缝补,与读者“一诉衷肠”,人害怕孤独,所以说话,但人无法脱离孤独,因为旧日子永远都在,使你摇摆在孤独和不孤独之间。《一句顶一万句》让我们在孤独中仍能感受到生命中的执着与顽强,找回对生活、对世界的热爱,直面孤独,不负人生。
故乡拨动你我的心弦
——《也傍桑阴书华年》里的精神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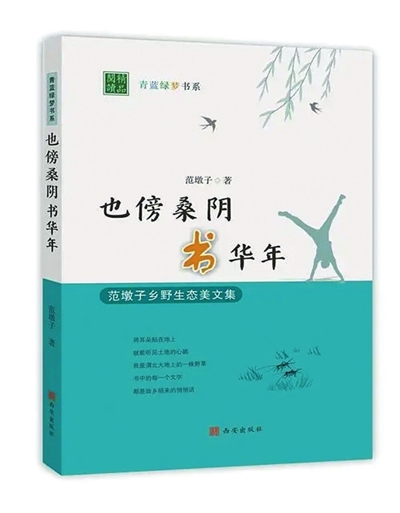
□ 鹿 离
对很多作家来说,故乡是永不枯竭的灵感之源,童年则是他们写作道路的起始点。作家范墩子的散文集《也傍桑阴书华年》延续其一贯灵动、质朴、诗意的语言风格,这一次他的情感流淌不再拘束、收敛,自然地捡拾其散落在山间草木上的童年音符,编织成一首献给故乡渭北大地的歌谣,悄悄撩拨你我记忆深处的心弦。
文学与故乡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当谈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时,范墩子如是说:“我是一个随时把童年记忆和故乡记忆携带在身上的人。”从短篇小说集《我从未见过麻雀》以孩童视角构筑新时代中国少年的“心灵史”,长篇小说《抒情时代》以“我”的视角讲述小镇少年从故乡走进城市的成长史,到儿童小说《去贝加尔》以成人视角描绘勇敢少年寻找希望与爱的故事,到如今的散文集《也傍桑阴书华年》从回望视角记录行走于故乡的所见所悟,即便范墩子自陈“已成为了故乡的局外人”,但他的写作从未离开童年和故乡,笔下常常出现麻雀、豹榆树、桑柘、牧羊人、唐陵遗迹等这些带有明显故乡标志的物事,字里行间处处藏着故乡的风物地理人情,故乡是他不可缺失的精神家园。
文学是故乡映在心田的影子,也是寄托深情的信仰。尽管他已走出乡村,到大城市扎根生活,可他的内心深处却迷恋着宁静淳朴的乡野生活,苍凉的大地、寂寥的山风、草木的微笑、河流的嗓音……当他将耳朵贴在地上,就能听见土地的心跳,而当他的心贴在地上,“我那遗失的睡梦就重新苏醒了过来,活了过来”。于他而言,只有将自己投入渭北大地的怀抱,细细回望和描摹故乡的风物人情,他的身心才能得到真正的放松。他在后记《从故乡出发的写作》中写道,“故乡是逼仄的,更是辽阔的”。童年时代的故乡风景,成为他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也成为他最初也是最成功的表现天地。他也说,“我是渭北土地上的一株野草”,将宁静山风中故乡捎来的悄悄话,写成审视故土过往和当下时代的文字,越写越朴素,越写越宽广。
每个人都有一片文学的故乡。范墩子对故乡满怀深情,一次又一次走在回乡的路途上,走进山间田野重温故乡的风土人情,也在行走中正视自己内心深处的复杂图景。从家乡出发的写作是一种精神还乡,也是一次次的精神回归之旅。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故乡的深深眷恋,直陈自己喜欢靠在豹榆树厚实的树身上,任斑驳的树影唤醒童年的记忆,感叹“每次看到贫瘠的塄坎上却长着许多开着花的小雏菊,我的心里都会涌出无限的感动”,他早已摆脱地理上的“狭隘的故乡概念”,可故乡依旧是他无法割舍的情结,无论是故乡黑暗的地方,还是故乡光明的地方。“童年是我写作的富矿”,书中收录多篇追忆童年往事的文章,文笔优美,情感质朴,但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滚铁环》一文,篇幅虽短,却令人感到亲切温暖,铁环也曾滚过我的童年时光,我也曾写过类似的文章。故乡的童年记忆有苦有甜,可当我们身在远方对家乡和童年深情凝眸时,内心深处的小天地总是充满温馨,不安的情绪得以慢慢平息,温暖溢满心头。故乡本是一个苦涩与美好共存的话题,他直面自我的故乡叙述中却鲜少苦涩的味道,更多的是纯净的美好。细细究之,他并非无视故乡的逼仄和荒凉,也不缺少审视的目光和勇气,而是在“一边厌倦着城市生活,又无法摆脱得开城市生活”的心理纠缠中,童年故乡的记忆成了他精神的栖息地,哪怕是苦涩的记忆也成为一种美好。
正如范墩子所言,我们已“很难再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返乡”,这是生活的无奈,也是自然的规律。故乡总是在不经意间拨动你我的心弦,当我们感到疲惫和孤单的时候,不妨多回家看看,望望归乡的路,哪怕只有一瞥,哪怕只是纸上故乡,都能感到母亲怀抱般的放松和温暖。
□ 张斯
“书读完了”,我盯着封面上这几个大字,生出些许困惑:古今中外,典籍如浩瀚宇宙之星辰,究竟是什么人敢口出狂言?我移目到署名处,金克木,困惑消散了多半。他以小学学历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传奇经历为大家所熟知。但学贯中西的金克木先生“宣称”书读完了,似乎与他一贯求知若渴、谦虚谨慎的治学理念背道而驰。然而我心中又升腾出希望,读完此书,是不是也能掌握些能将书读完的技巧。
金克木先生提出了“书可以读完”的依据:“把书读完”首先是要读什么书,每一种文化都有几部最重要的文献经典,它们既不依附于其他书,又是整个系统的知识基础,把中外文化中的这类书通读之后,就可以说是“书读完了”。他列出根源性典籍,以中国为例,他认为不读《周易》《诗经》《尚书》《左传》《礼记》《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就无法读韩愈、朱熹的书,就连《西厢记》《红楼梦》中的词句用典也无法体会。他还分享了几种读书方法:把作者、书籍当成朋友,谈论式、质疑式的福尔摩斯读书法;读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读书空白内容,思考文字弦外之音的读书得间法;读书、读人、读物的方法。
《读书·读人·读物》中道:“一本书若满是字,岂不是一片油墨?没有空白是不行的,像下围棋一样。古人、外国人、现代人作书,好像是都不会把话说完、说尽的,不是说他们‘惜墨如金’,而是说他们无论有意无意都说不尽要说的话。越是啰嗦废话多,越说明他有话说不出或是还没有说出来。那只说几句话的就更是话里有话了。”要想读懂书中的真意,不光要看说了什么,更要看什么没说。有人认为,“当于无字处求之”的读书方法,有过度解读之嫌。但文学创作中,追求言外之意是中国文化的独特精神。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隐秀”的创作理念,被现代国学大师黄侃冠之“文苑最要”。简单来说,隐是字面意义之外的内容,秀是作品中出类拔萃的句子。一部作品如果不包含意蕴丰富的韵味、悠远隽永的意趣、触类旁通的情感,就不能被称为佳作,而以上都只能通过有限的言辞以及言辞之外的空白来营造。要想准确掌握优秀作品中的言外之旨,就需要如金克木先生所说,要将蕴含文明根源性的典籍通读熟读,带着问题与作者对话。
贾岛与韩愈在“推敲”上反复斟酌,这是创作者对言外之意能否准确传达的琢磨。读者若是知晓贾岛曾落魄出家,却又想建功立业的心路历程,就能更好地体会到“僧敲月下门”的克己复礼和目盼心思。在书中所占篇幅不多的“风月宝鉴”为何能成为《红楼梦》的别称?只有体会书中风月宝鉴正面红粉佳人、背面骷髅恶鬼的含义,结合中国传统“正衣冠、知兴替、明得失、辟不祥、驱邪恶”的镜文化,方能体会到深隐在人物背后的尔虞我诈、四大家族的处心积虑,乃至时代的困顿无力。
书读完了,我只掌握了九牛一毛,但也受益匪浅。我穷极一生,也无法达到金克木先生的境界,只能在有限的时间用学到的方法竭尽所能地读懂书,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
书,读不完;读懂,也是妙事。
□ 黄 泰
《繁花》改编自作家金宇澄的同名小说,由王家卫导演,胡歌、马伊琍、游本昌、唐嫣、辛芷蕾、郑恺等主演。全剧聚焦20世纪90年代初以阿宝为代表的普通人在沪上风云际会的生意场中追逐机遇,努力改变自我的成长故事。
在风云变幻的资本市场、复杂的人性、微妙的情感等元素的交织下,《繁花》展现出了极具历史激情和现实感染力的故事,深深地吸引着观众的心。这部剧凭借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和深刻的主题,为观众带来了深刻而真实的震撼,让人深受感动。
进入电视剧《繁花》的世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精致的视觉美感。导演王家卫善于用色彩来衬托故事,借此铺陈演员与故事间的情调。剧中的影像充满了希望和生机,当中不乏对寻常生活、市井姿态的书写:进贤路的拥挤与热闹,华灯初上的黄河路等,带观众细细品味迷离光影下的上海。高度的影像还原,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切身感受到上海的繁华和活力。
在剧中,游本昌扮演的爷叔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纽约的帝国大厦晓得吧,从底下跑到屋顶要一个钟头,从屋顶跳下来,只要八点八秒。”这句话暗示了生意场的残酷现实,凸显他作为阿宝的合伙人所具备的深思远虑和长远目光,也显示出老一代上海人对年轻一代的独特栽培方式与期望。关于阿宝,对他而言最具代表性的词便是“不响”。他说:“做生意,首先要学会两个字:不响。不知道的,说不清楚的,没想好、没规划的,为难自己、为难别人的,都不响。”“不响”,在《繁花》原著出现过多次,它意味悠长,犹如一种沉默的留白。王家卫说:“是什么让阿宝成为宝总,一夜之间成为时代弄潮儿,书里没有体现,我们可以‘补白’。”阿宝有着盖茨比般的派头,他成功过,也失败过,总是激情澎湃且充满信心,有着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和希望。他同千千万万个在上海奋斗的人一样,起起落落,亦如繁花一样花开花落。
剧中对玲子、汪小姐、李李等女性人物角色的表现是一大亮点。玲子嘴硬心软、精打细算,王小姐开朗动人、倔强坚定,李李雷厉风行、智慧干练。用原著《繁华》的句子形容最为令人动容:“一个女人,越是笑容满面,欢天喜地,一翻底牌,越是苦,一肚皮苦水。”除了聚焦这些抢眼的人物外,导演还精心刻画了配角群像,比如冷静的金科、心比天高的小江西,以及脚踏实地、善解人意的露丝。她们身处不同的社会阶层,可她们代表着时代浪潮中在沪奋斗女性不同的外在与智慧,也呈现出她们各具特色的魅力与生命力,让上海这座城市更加鲜活和真实。
在该剧的创作过程中,导演王家卫并非单纯地照搬原著,而是通过自己的独有的方式还原了《繁花》的气质和灵魂,让原著中的阿宝等人物活了起来,增强了故事性并重新处理了叙事节奏,让电视剧和文学互相借力,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电视剧《繁花》从光影到叙事都不乏王家卫式的浪漫维度与格调,他用自己的方式与原著默契配合,让剧中的人物发光发亮,充实了《繁花》的灵与肉。全剧让我们品味到浓郁的上海文化历史韵味和群体奋斗的精神风貌,为我们呈现了一场充满沪上烟火气息的视觉盛宴。
□ 孙功俊
墙上挂着一把锄,身影逐渐斑驳,诸多的陈年往事锈进了岁月里。
所有的经过都有记忆,一把锄也不例外。
那些锄过的杂草,锈进曾经的梦里;那些大豆、花生、芝麻、红薯经过的夏天,锈进远处的风景;那些春天飞起的柳丝,锈进旧时的斑斓。
父亲已经走远,荷锄人无法从时空中返回。
挂在墙上的一把锄,只能木然地看着自己的锈迹斑斑。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