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潘渊之

珠海传媒集团 刘轶男摄
3月17日,推出ChatGPT的人工智能实验室OpenAI,发布了一份关于“大型语言模型对劳动力市场潜在影响”的研究报告,将作家列入受ChatGPT影响最大的职业——这里说的“影响”,可以从“攸关生死”的层面理解。但我接触到的公开报道中,中国作家普遍没有表现出“全员下岗”的焦虑感。相反,一些科幻小说、网络文学界的作家,已经把人工智能作为角色写入作品,甚至在尝试借助AI来写作了。比如“80后”科幻作家陈楸帆,在ChatGPT引发热议之前,就在小说集《人生算法》中实验了人工智能写作,并对其表现非常认可。
另一位“80后”作家双雪涛则似乎有点无奈。他认为,作家们真正的危机,会在“AI拥有读者、人类为它的作品买单”的时候出现,“那时候我也改变不了什么。我能改变什么?我只能去写自己的东西,接受一个手工业者的命运。”
3月26日,在华东师大举办的“现实与传奇:王安忆、余华对谈”上,谈到人工智能,王安忆说:“人工智能能够写作,那我们干什么?我想了一下还是写作,我们能从写作本身获得的乐趣无法取代。更何况生活有时候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余华接过话头:“生活不是按常理出牌的,这是我们打败人工智能的武器。”他认为,“人脑总是要犯点错的,这也是可贵之处。当ChatGPT接近完美、没有缺点时,也就没有了优点;它对我和王安忆来说,起码是构不成威胁的。”他推断,就算ChatGPT能写小说,大概也是“中庸而非个性”的小说。
或求诸自己(写作有乐趣),或假于外物(完美即不足),王安忆和余华这种名满天下的成熟作家,还有更多的理由在ChatGPT的潜在威胁面前保持风度。在可见的未来,AI大概率不会具备比他们还优秀的写作能力——要知道,它成长的途径之一,就是以他们的作品为学习、模仿的范本。
但是,生活毕竟“不按常理出牌”,总有不确定因素伺机而动。比如,AI会不会真的像双雪涛说的那样拥有了读者,且读者的阅读趣味发生匪夷所思、不可预测的转向呢?如果AI拆掉了写作的门槛,使人都能借助它生成自己的小说散文,以致无需阅读别人的作品,就能满足精神生活,那么,作家这个职业,就真的到了面对“哈姆莱特之问”的时候了。
在与王安忆对谈时,余华讲了他接触人工智能的一次经历。他用国内的人工智能搜索过“文学是什么?”“文学有什么意义?”两个问题。
关于“文学是什么”,文心一言的答案则是百度百科的精华版。再问“文学有什么意义”,文心一言归纳为五条,以各条所属类别引领正文,更像中文系教材。它们也都没给出“文学是人学”“文学就是文学之所以称之为文学的东西”“文学是作者与读者的交流,是作者经验、素养与感受、思考的交流”这样虽不严谨但有“文学性”的回答。
“余华二问”的命题太大,应属文学本体论范畴。它们很重要,但你知道或不知道,与你能否写出好小说没太大关系。我想,余华不过是随便问问,未必很在乎答案。

潘渊之 《文学自由谈》杂志主编。从事期刊编辑工作三十余年,编而不作。职责之内,甲乙丙丁;本分之外,乏善可陈。惭愧!
星空(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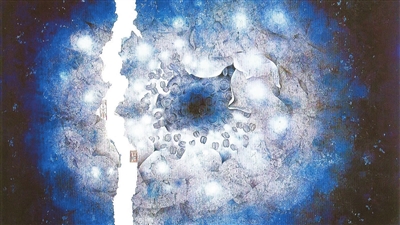
刘春潮 作品


□ 王威廉

珠海传媒集团 刘轶男摄
《有数》是近期对我触动最大的一本书。
如果要为21世纪以来这二十年的历史发展找到一个关键词,我想“数字化”一定会获得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在回顾之际,我们清晰看到:在第一个十年,网络技术从少数科研、军工领域向民间开放,它的现代信息工具的属性备受瞩目,上网被喻为“冲浪”,寓意为时代弄潮儿,引领的是一种社会时尚,因此,网络往往被理解成一个跟现实不同的新空间;而在移动网络技术为基础的第二个十年,网络已经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个毛细血管当中,我们在网络中的一切交互痕迹也变成了“大数据”的一部分,进一步催化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
因此,“数字化”犹如江河入海,层层浸润,愈发壮阔。从数字经济到数字社会,而现在,我们已经置身于数字文化当中。“数字化”以极短的时间便已内化为人类的基本生活方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文明发展的重要向度。
我是一名作家,困扰我最多的一个概念便是“现实”。各种文学流派、创作手法都是围绕着对“现实”的理解而开展的,而新的现实已经诞生,大多数人却习焉不察。很多人还是有种思维定势,觉得现实生活就是现实生活,网络是数字化的工具,两者可以分得很清。但现实跟虚拟的关系早已失去了边界。我们用百度地图搜索定位一家餐厅,然后用软件叫车抵达,扫桌面上的二维码点餐,再扫码买单,闲了还可发个朋友圈……这是一整套链条,现实跟线上完全揉在一起,是难以分离的。手机犹如人们的外挂器官,手机没电关机或没有信号的时刻,焦虑会立即潮涌,个人觉得被一种整体性的东西忽然抛弃了,流放到一种不安全、不可靠的孤独当中。
这样的情形如此普遍而隐秘,深深塑造着当代人的精神世界。我们不能再固守前见,我们必须得深入其中,才能真正理解它的构成与趋势。我早就心心念念着,何时才会有一本走出书斋,深入数字社会、数字文化的调研考察之书。
《有数》就是这么一本书。
温铁军先生在书的跋中写道:“要尽可能通过直接调查研究去得出自己的结论。唯有如此,才能不被纷繁复杂的信息中那些垃圾和病毒所蒙蔽,避免被这些所谓信息背后的推手牵着走而不自知。”他就是一个“用脚做学问的人”,这不仅是说用脚走得远,更是意味着要走近乃至走进那些对象的生活深处。
于是,我在《有数》中看到了我们时代的人生。人们如何利用“数字化”来改变自己的人生,这样的故事我们并不陌生,在新闻里,在街谈巷议里,我们都听说过,但我们谈论的大多都是马云、马化腾这类少数精英,没人理会书中提到的老甘、张宇等“野生码农”。而正是这些普通人的名字、普通人的面孔、普通人的生活,让他们突破了符号的遮蔽,我们瞬忽发现,他们的人生就是我们自己的寓言。
我还看到了我们时代的现实。在前文已经提到,传统现实与数字现实混合构成了一个更大的现实,这个新现实的力量如此巨大,以至改变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城市、精英已不再是舞台中心的全部,广大的乡镇边地、普通人也获得了新的照亮:只要他们有个性、有想法、有故事,都可以在这个大现实中展现自己,并有机会来到舞台的中央。正如书中引述建筑师库哈斯的话:“对于乡村,我格外看重数字技术在其中起到的变革性作用。世界的未来在乡村。”
毫不夸张地说,我竟然还看到了奇迹。我从未想到世间还有盲人程序员,那个叫沈广荣的广州人,1996年出生,天生全盲,从小到大别人都告诉他,你要学好按摩,因为那是盲人的唯一前途,但数字技术给予他新的梦想,他不仅证明了自己,还打破了偏见,原来盲人也能编程,也能反哺数字技术。
复杂的感触更是源源不绝。我从未想到手机可以如此深入地改变家庭成员的关系以及教育方式,母亲跟手机抢夺着孩子的爱。这个虚拟的端口,抽空了此间的实在之物,让贫乏更显贫乏,但同时又为我们敞开了一个高尚与低俗混杂沸腾的信息海洋。摧毁与建设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而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却无法定义何为摧毁、何为建设,这分明是一种未来文化的雏形。
我意识到,人与数字技术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工具性的,更是生存性的,这才是最根本的改变。数字技术应用于生活中的无数细节,已经让我们忽略了数字技术本身,它已经构成了当代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如同呼吸一般,时时刻刻,却不用去额外觉察。这也意味着今后这方面的调研将会有更大难度,数字文化不再是容易辨别的“异”,而是水乳交融的“同”。
也正是这样的背景,有了“元宇宙”这样的流行概念。我在《有数》的封面上,看到编写组给自己起名叫“数字原野工作室”,我特别喜欢“数字原野”这个意象。如此诗意,如此准确,比“元宇宙”这个概念黑洞要好得多。毋庸置疑,还有太多可能性在这片原野上孕育着。书的英文名是Tech for Good,技术让我们更好。技术原本是中性的,有恰当机制的催化与巩固,就会爆发出它作为生产力的能量,大幅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
这次数字技术革命,是对每个人的生活乃至生命的拓宽,就像它的副标题:普通人的数字生活纪实。普通人这点格外重要,因为信息资源在人类过去数千年的文明史当中都属于少数人,那些金字塔尖的统治阶层。但是今天,这种资源向所有人敞开,它让每个人可以建构起以自身为塔尖的信息帝国,而信息意味着智慧,意味着可能,意味着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空间恰恰就是人类那个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精神空间。
我们无庸讳言,数字生活不全是美好的,我从不否定数字技术也会带来巨大的晦暗,比如公共文化的危机,但是这些相比于人类精神世界的自由来说,是值得的。这过去的二十年,还有未来的二十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转折点。面临这样的重要时刻,面对这样的历史关口,我们确实要“心中有数”。

王威廉 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教研室主任,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小说《野未来》《内脸》《非法入住》《听盐生长的声音》《倒立生活》等,部分作品译为英、韩、日、意、匈等文字在海外出版。曾获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十月文学奖、花城文学奖等数十个文学奖项。
长白山的白
(组诗)
□ 梁 平

珠海传媒集团 刘轶男摄
绝版
绝版。一条毛线围巾沾满地气,
手指穿针引线,在夜色中,
把上弦月的缺口织满。
没有任何一条线路可以抄袭,
天上掉下的流星,一千零一颗,
每一颗都是隐喻。
以后再多的款式和品牌,黯然失色,
再也没有它的质地和温暖。
涅瓦河那年的白夜,围巾包裹,
一针针辨认线条行走的路径,
还是那手指,开始给时间占卜——
洗牌的正逆和开牌的方位,
与围巾起伏的波涛不谋而合,
刻意留下的漏针显赫,那是天眼。
呼吸在缝隙的通道起承转合,
针眼里一朵隐身的雪,光芒闪耀,
还是那么生动。
文笔峰密码
一只没有祖籍的鸟,锋利的羽毛,
划破水成岩石褶皱里的睡眠。
文笔峰在天地之间举一支巨椽,
披挂唐宋元明囤积的风水,
比身边的海更浩荡。
皇家禁苑的清净,
匹配白玉蟾仙风道骨的虚空,
王子脚印垫高海拔,将军横马立刀。
峰顶无形无象,太极辽阔了沧海桑田。
天的边际,一朵云飘然而至,
有麻姑的仙姿。
而这些文墨只是印记,
子虚乌有的鸟,那只得道的鸟,
留一阕如梦令在海南。
道场深不可测,沉香弥漫,
笔尖上做一次深呼吸,云淡风轻。
长白山的白
我之前,康熙、乾隆和嘉庆,
在长白山褶皱里走过御笔,
文字卷起飞雪,比玉玺的鲜红耀眼,
雨燕束腰,峰峦拔节。
长白山的白,
留给我的辽阔,与我的深入浅出,
如此匹配。远古火山口最初的临盆,
脐带上的血也是白色。
黑风口垂帘的瀑布,
天池游弋的云朵,不能轻描淡写,
纯净的白,容不下虚情假意。
很多人想把脚印留在山上,
一阵风过无踪无影。
沿北坡攀援,岳桦林带的集体匍匐,
把对雪的膜拜书写成经典。
所有趾高气昂在这里,
没有立足之地,所有轻浮和潦草,
所有廉价的颂辞一文不值。
长白山的白,留得明明白白,
即使季节改变各种颜色,
那白,在心底,根深蒂固。

梁平 当代诗人、编辑。著有诗集、散文随笔、诗歌批评十余卷。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成都市文联名誉主席、《草堂》诗刊主编。现居成都。
□ 周 实

珠海传媒集团 刘轶男摄
躲来躲去,还是“阳”了,是祸躲不过。“阳”了怎么办?医生说躺平,休息是最好的治疗方法。这就像当年有人说的,会休息才会工作,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躺平就是会休息。
躺平这个词是近两年来走红网络的流行词。据百度百科词语解释,其意思大概指:无论对方做出什么反应,你内心都毫无波澜,对此不会有任何反应或者反抗,表示顺从心理。另外,在部分语境中表示为:瘫倒在地,不再鸡血沸腾,渴求成功了。躺平看似是妥协放弃,其实是“向下突破天花板”,选择最无所作为的方式反叛裹挟。年轻人选择躺平,就是选择走向边缘,超脱于加班、升职、挣钱、买房的主流路径之外,用自己的方式消解外在环境对个体的规训。读着百度百科的解释,须发飘扬的商山四皓从那远古向我走来,除了老子、庄子之外,他们四位在我心里算得是躺平的老祖宗了。
汉高帝刘邦十一年(前196年)七月间,淮南王黥布造反。刘邦(前256-前195年)身体不适,想派太子(刘盈,前211-前188年)统领大军进行讨伐。太子的家客商山四皓(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为避秦祸,曾隐商山,即今陕西丹凤县内),听说之后,极力反对,并劝吕后对皇帝说:“黥布天下猛将,很会用兵。今诸将都是皇帝从前交往的朋友,要太子去带领他们,恐怕他们不肯用命。皇帝虽然有点病,若能勉强坐在车上,监督各军,诸将不敢不尽力。这样皇帝虽苦一点,却也是为妻子天下而不能不自强的事情。”高帝听了,当然气忿,终也只好叹口气说:“我知小子不中用,老子自己去打吧!”黥布自然被打败了,落荒而逃,最后死于乡民刀下。
商山四皓为什么不愿太子出征呢?因为太子打胜了回来依旧是太子,若是万一打败了,高帝正好借口废立。那时候,无论谁,恐也无能为力了。
四皓究竟是何人呢?史书上也只有大概。东园公姓唐,字宣明,居于园中,因以为号。绮里季住在绮里,字名季,或姓朱名晖。再其次是夏黄公,因避秦祸,藏于商山,本姓崔名广字少通,原住在夏里,故号夏黄公。至于甪里老先生,查也很难查出姓氏,当然也是商山隐士。
四皓后来又怎样了?史书上也没有记载,只有唐人牛僧孺的《玄怪录》中有一小文,题为《巴邛人》,稍稍透露了一点信息:有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园,打霜后,橘子尽收,只剩两个,非常大,犹如三四斗的罐子。巴人异之,即令攀摘,轻重亦如常橘,剖开,每橘有二老叟,须眉皤然,肌体红润,身仅尺余,谈笑自若,相对而坐,下着象棋,剖开后也毫不惊慌,继续博弈。一叟曰:“王先生答应来,终究是等不及了。橘中的乐趣,与商山相比虽不减色,可惜不能深根固蒂,还是让人家给摘下来了。”此事似在隋唐之间,却又没有具体年号。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孝惠帝后,商山四皓就“躺平”在深山里了,甚至“躺”在这橘子里。不过,即便如此,还是被人摘了下来。
躺平也是要条件的,偶尔也会被打断的,长久更是不可能的。人生苦短,时间有限,哪怕你是一个仙人。
躺平也分消极积极。消极的躺平以卑微的心态、渺小的姿态,但求能够与世无争。积极的躺平是疗伤静养,恢复充电,以退为进,无论生存状态怎样,都要做一个大写的人。

周实 编审,湖南长沙人,曾创办《书屋》并任主编。主要作品有诗集《剪影》,短篇小说集《刀俎》,长篇散文《无法安宁》,长篇诗文《写给Phoebe的繁星之夜》,长篇随笔《老先生》《一个人在书房里》,长篇小说《闲人外传》等。


□ 潘渊之

珠海传媒集团 刘轶男摄
3月17日,推出ChatGPT的人工智能实验室OpenAI,发布了一份关于“大型语言模型对劳动力市场潜在影响”的研究报告,将作家列入受ChatGPT影响最大的职业——这里说的“影响”,可以从“攸关生死”的层面理解。但我接触到的公开报道中,中国作家普遍没有表现出“全员下岗”的焦虑感。相反,一些科幻小说、网络文学界的作家,已经把人工智能作为角色写入作品,甚至在尝试借助AI来写作了。比如“80后”科幻作家陈楸帆,在ChatGPT引发热议之前,就在小说集《人生算法》中实验了人工智能写作,并对其表现非常认可。
另一位“80后”作家双雪涛则似乎有点无奈。他认为,作家们真正的危机,会在“AI拥有读者、人类为它的作品买单”的时候出现,“那时候我也改变不了什么。我能改变什么?我只能去写自己的东西,接受一个手工业者的命运。”
3月26日,在华东师大举办的“现实与传奇:王安忆、余华对谈”上,谈到人工智能,王安忆说:“人工智能能够写作,那我们干什么?我想了一下还是写作,我们能从写作本身获得的乐趣无法取代。更何况生活有时候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余华接过话头:“生活不是按常理出牌的,这是我们打败人工智能的武器。”他认为,“人脑总是要犯点错的,这也是可贵之处。当ChatGPT接近完美、没有缺点时,也就没有了优点;它对我和王安忆来说,起码是构不成威胁的。”他推断,就算ChatGPT能写小说,大概也是“中庸而非个性”的小说。
或求诸自己(写作有乐趣),或假于外物(完美即不足),王安忆和余华这种名满天下的成熟作家,还有更多的理由在ChatGPT的潜在威胁面前保持风度。在可见的未来,AI大概率不会具备比他们还优秀的写作能力——要知道,它成长的途径之一,就是以他们的作品为学习、模仿的范本。
但是,生活毕竟“不按常理出牌”,总有不确定因素伺机而动。比如,AI会不会真的像双雪涛说的那样拥有了读者,且读者的阅读趣味发生匪夷所思、不可预测的转向呢?如果AI拆掉了写作的门槛,使人都能借助它生成自己的小说散文,以致无需阅读别人的作品,就能满足精神生活,那么,作家这个职业,就真的到了面对“哈姆莱特之问”的时候了。
在与王安忆对谈时,余华讲了他接触人工智能的一次经历。他用国内的人工智能搜索过“文学是什么?”“文学有什么意义?”两个问题。
关于“文学是什么”,文心一言的答案则是百度百科的精华版。再问“文学有什么意义”,文心一言归纳为五条,以各条所属类别引领正文,更像中文系教材。它们也都没给出“文学是人学”“文学就是文学之所以称之为文学的东西”“文学是作者与读者的交流,是作者经验、素养与感受、思考的交流”这样虽不严谨但有“文学性”的回答。
“余华二问”的命题太大,应属文学本体论范畴。它们很重要,但你知道或不知道,与你能否写出好小说没太大关系。我想,余华不过是随便问问,未必很在乎答案。

潘渊之 《文学自由谈》杂志主编。从事期刊编辑工作三十余年,编而不作。职责之内,甲乙丙丁;本分之外,乏善可陈。惭愧!
星空(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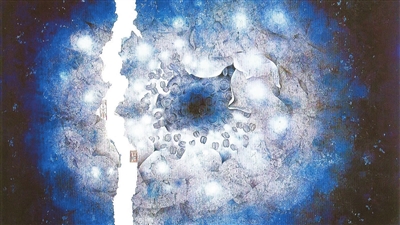
刘春潮 作品


□ 王威廉

珠海传媒集团 刘轶男摄
《有数》是近期对我触动最大的一本书。
如果要为21世纪以来这二十年的历史发展找到一个关键词,我想“数字化”一定会获得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在回顾之际,我们清晰看到:在第一个十年,网络技术从少数科研、军工领域向民间开放,它的现代信息工具的属性备受瞩目,上网被喻为“冲浪”,寓意为时代弄潮儿,引领的是一种社会时尚,因此,网络往往被理解成一个跟现实不同的新空间;而在移动网络技术为基础的第二个十年,网络已经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个毛细血管当中,我们在网络中的一切交互痕迹也变成了“大数据”的一部分,进一步催化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
因此,“数字化”犹如江河入海,层层浸润,愈发壮阔。从数字经济到数字社会,而现在,我们已经置身于数字文化当中。“数字化”以极短的时间便已内化为人类的基本生活方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文明发展的重要向度。
我是一名作家,困扰我最多的一个概念便是“现实”。各种文学流派、创作手法都是围绕着对“现实”的理解而开展的,而新的现实已经诞生,大多数人却习焉不察。很多人还是有种思维定势,觉得现实生活就是现实生活,网络是数字化的工具,两者可以分得很清。但现实跟虚拟的关系早已失去了边界。我们用百度地图搜索定位一家餐厅,然后用软件叫车抵达,扫桌面上的二维码点餐,再扫码买单,闲了还可发个朋友圈……这是一整套链条,现实跟线上完全揉在一起,是难以分离的。手机犹如人们的外挂器官,手机没电关机或没有信号的时刻,焦虑会立即潮涌,个人觉得被一种整体性的东西忽然抛弃了,流放到一种不安全、不可靠的孤独当中。
这样的情形如此普遍而隐秘,深深塑造着当代人的精神世界。我们不能再固守前见,我们必须得深入其中,才能真正理解它的构成与趋势。我早就心心念念着,何时才会有一本走出书斋,深入数字社会、数字文化的调研考察之书。
《有数》就是这么一本书。
温铁军先生在书的跋中写道:“要尽可能通过直接调查研究去得出自己的结论。唯有如此,才能不被纷繁复杂的信息中那些垃圾和病毒所蒙蔽,避免被这些所谓信息背后的推手牵着走而不自知。”他就是一个“用脚做学问的人”,这不仅是说用脚走得远,更是意味着要走近乃至走进那些对象的生活深处。
于是,我在《有数》中看到了我们时代的人生。人们如何利用“数字化”来改变自己的人生,这样的故事我们并不陌生,在新闻里,在街谈巷议里,我们都听说过,但我们谈论的大多都是马云、马化腾这类少数精英,没人理会书中提到的老甘、张宇等“野生码农”。而正是这些普通人的名字、普通人的面孔、普通人的生活,让他们突破了符号的遮蔽,我们瞬忽发现,他们的人生就是我们自己的寓言。
我还看到了我们时代的现实。在前文已经提到,传统现实与数字现实混合构成了一个更大的现实,这个新现实的力量如此巨大,以至改变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城市、精英已不再是舞台中心的全部,广大的乡镇边地、普通人也获得了新的照亮:只要他们有个性、有想法、有故事,都可以在这个大现实中展现自己,并有机会来到舞台的中央。正如书中引述建筑师库哈斯的话:“对于乡村,我格外看重数字技术在其中起到的变革性作用。世界的未来在乡村。”
毫不夸张地说,我竟然还看到了奇迹。我从未想到世间还有盲人程序员,那个叫沈广荣的广州人,1996年出生,天生全盲,从小到大别人都告诉他,你要学好按摩,因为那是盲人的唯一前途,但数字技术给予他新的梦想,他不仅证明了自己,还打破了偏见,原来盲人也能编程,也能反哺数字技术。
复杂的感触更是源源不绝。我从未想到手机可以如此深入地改变家庭成员的关系以及教育方式,母亲跟手机抢夺着孩子的爱。这个虚拟的端口,抽空了此间的实在之物,让贫乏更显贫乏,但同时又为我们敞开了一个高尚与低俗混杂沸腾的信息海洋。摧毁与建设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而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却无法定义何为摧毁、何为建设,这分明是一种未来文化的雏形。
我意识到,人与数字技术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工具性的,更是生存性的,这才是最根本的改变。数字技术应用于生活中的无数细节,已经让我们忽略了数字技术本身,它已经构成了当代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如同呼吸一般,时时刻刻,却不用去额外觉察。这也意味着今后这方面的调研将会有更大难度,数字文化不再是容易辨别的“异”,而是水乳交融的“同”。
也正是这样的背景,有了“元宇宙”这样的流行概念。我在《有数》的封面上,看到编写组给自己起名叫“数字原野工作室”,我特别喜欢“数字原野”这个意象。如此诗意,如此准确,比“元宇宙”这个概念黑洞要好得多。毋庸置疑,还有太多可能性在这片原野上孕育着。书的英文名是Tech for Good,技术让我们更好。技术原本是中性的,有恰当机制的催化与巩固,就会爆发出它作为生产力的能量,大幅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
这次数字技术革命,是对每个人的生活乃至生命的拓宽,就像它的副标题:普通人的数字生活纪实。普通人这点格外重要,因为信息资源在人类过去数千年的文明史当中都属于少数人,那些金字塔尖的统治阶层。但是今天,这种资源向所有人敞开,它让每个人可以建构起以自身为塔尖的信息帝国,而信息意味着智慧,意味着可能,意味着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空间恰恰就是人类那个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精神空间。
我们无庸讳言,数字生活不全是美好的,我从不否定数字技术也会带来巨大的晦暗,比如公共文化的危机,但是这些相比于人类精神世界的自由来说,是值得的。这过去的二十年,还有未来的二十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转折点。面临这样的重要时刻,面对这样的历史关口,我们确实要“心中有数”。

王威廉 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教研室主任,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小说《野未来》《内脸》《非法入住》《听盐生长的声音》《倒立生活》等,部分作品译为英、韩、日、意、匈等文字在海外出版。曾获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十月文学奖、花城文学奖等数十个文学奖项。
长白山的白
(组诗)
□ 梁 平

珠海传媒集团 刘轶男摄
绝版
绝版。一条毛线围巾沾满地气,
手指穿针引线,在夜色中,
把上弦月的缺口织满。
没有任何一条线路可以抄袭,
天上掉下的流星,一千零一颗,
每一颗都是隐喻。
以后再多的款式和品牌,黯然失色,
再也没有它的质地和温暖。
涅瓦河那年的白夜,围巾包裹,
一针针辨认线条行走的路径,
还是那手指,开始给时间占卜——
洗牌的正逆和开牌的方位,
与围巾起伏的波涛不谋而合,
刻意留下的漏针显赫,那是天眼。
呼吸在缝隙的通道起承转合,
针眼里一朵隐身的雪,光芒闪耀,
还是那么生动。
文笔峰密码
一只没有祖籍的鸟,锋利的羽毛,
划破水成岩石褶皱里的睡眠。
文笔峰在天地之间举一支巨椽,
披挂唐宋元明囤积的风水,
比身边的海更浩荡。
皇家禁苑的清净,
匹配白玉蟾仙风道骨的虚空,
王子脚印垫高海拔,将军横马立刀。
峰顶无形无象,太极辽阔了沧海桑田。
天的边际,一朵云飘然而至,
有麻姑的仙姿。
而这些文墨只是印记,
子虚乌有的鸟,那只得道的鸟,
留一阕如梦令在海南。
道场深不可测,沉香弥漫,
笔尖上做一次深呼吸,云淡风轻。
长白山的白
我之前,康熙、乾隆和嘉庆,
在长白山褶皱里走过御笔,
文字卷起飞雪,比玉玺的鲜红耀眼,
雨燕束腰,峰峦拔节。
长白山的白,
留给我的辽阔,与我的深入浅出,
如此匹配。远古火山口最初的临盆,
脐带上的血也是白色。
黑风口垂帘的瀑布,
天池游弋的云朵,不能轻描淡写,
纯净的白,容不下虚情假意。
很多人想把脚印留在山上,
一阵风过无踪无影。
沿北坡攀援,岳桦林带的集体匍匐,
把对雪的膜拜书写成经典。
所有趾高气昂在这里,
没有立足之地,所有轻浮和潦草,
所有廉价的颂辞一文不值。
长白山的白,留得明明白白,
即使季节改变各种颜色,
那白,在心底,根深蒂固。

梁平 当代诗人、编辑。著有诗集、散文随笔、诗歌批评十余卷。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成都市文联名誉主席、《草堂》诗刊主编。现居成都。
□ 周 实

珠海传媒集团 刘轶男摄
躲来躲去,还是“阳”了,是祸躲不过。“阳”了怎么办?医生说躺平,休息是最好的治疗方法。这就像当年有人说的,会休息才会工作,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躺平就是会休息。
躺平这个词是近两年来走红网络的流行词。据百度百科词语解释,其意思大概指:无论对方做出什么反应,你内心都毫无波澜,对此不会有任何反应或者反抗,表示顺从心理。另外,在部分语境中表示为:瘫倒在地,不再鸡血沸腾,渴求成功了。躺平看似是妥协放弃,其实是“向下突破天花板”,选择最无所作为的方式反叛裹挟。年轻人选择躺平,就是选择走向边缘,超脱于加班、升职、挣钱、买房的主流路径之外,用自己的方式消解外在环境对个体的规训。读着百度百科的解释,须发飘扬的商山四皓从那远古向我走来,除了老子、庄子之外,他们四位在我心里算得是躺平的老祖宗了。
汉高帝刘邦十一年(前196年)七月间,淮南王黥布造反。刘邦(前256-前195年)身体不适,想派太子(刘盈,前211-前188年)统领大军进行讨伐。太子的家客商山四皓(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为避秦祸,曾隐商山,即今陕西丹凤县内),听说之后,极力反对,并劝吕后对皇帝说:“黥布天下猛将,很会用兵。今诸将都是皇帝从前交往的朋友,要太子去带领他们,恐怕他们不肯用命。皇帝虽然有点病,若能勉强坐在车上,监督各军,诸将不敢不尽力。这样皇帝虽苦一点,却也是为妻子天下而不能不自强的事情。”高帝听了,当然气忿,终也只好叹口气说:“我知小子不中用,老子自己去打吧!”黥布自然被打败了,落荒而逃,最后死于乡民刀下。
商山四皓为什么不愿太子出征呢?因为太子打胜了回来依旧是太子,若是万一打败了,高帝正好借口废立。那时候,无论谁,恐也无能为力了。
四皓究竟是何人呢?史书上也只有大概。东园公姓唐,字宣明,居于园中,因以为号。绮里季住在绮里,字名季,或姓朱名晖。再其次是夏黄公,因避秦祸,藏于商山,本姓崔名广字少通,原住在夏里,故号夏黄公。至于甪里老先生,查也很难查出姓氏,当然也是商山隐士。
四皓后来又怎样了?史书上也没有记载,只有唐人牛僧孺的《玄怪录》中有一小文,题为《巴邛人》,稍稍透露了一点信息:有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园,打霜后,橘子尽收,只剩两个,非常大,犹如三四斗的罐子。巴人异之,即令攀摘,轻重亦如常橘,剖开,每橘有二老叟,须眉皤然,肌体红润,身仅尺余,谈笑自若,相对而坐,下着象棋,剖开后也毫不惊慌,继续博弈。一叟曰:“王先生答应来,终究是等不及了。橘中的乐趣,与商山相比虽不减色,可惜不能深根固蒂,还是让人家给摘下来了。”此事似在隋唐之间,却又没有具体年号。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孝惠帝后,商山四皓就“躺平”在深山里了,甚至“躺”在这橘子里。不过,即便如此,还是被人摘了下来。
躺平也是要条件的,偶尔也会被打断的,长久更是不可能的。人生苦短,时间有限,哪怕你是一个仙人。
躺平也分消极积极。消极的躺平以卑微的心态、渺小的姿态,但求能够与世无争。积极的躺平是疗伤静养,恢复充电,以退为进,无论生存状态怎样,都要做一个大写的人。

周实 编审,湖南长沙人,曾创办《书屋》并任主编。主要作品有诗集《剪影》,短篇小说集《刀俎》,长篇散文《无法安宁》,长篇诗文《写给Phoebe的繁星之夜》,长篇随笔《老先生》《一个人在书房里》,长篇小说《闲人外传》等。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