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徐 迅

图源:新华社
春丢一粒籽,夏发万棵芽,咿子呀子哟……黄梅小调唱得好像就是蚕豆。很多年以来,蚕豆就是这样生长在南方的田间地头。乡亲们仿佛知道蚕豆有很强的生命力,很少大面积种植,而是漫不经心地在插完秧后,顺手一溜地撒落在田埂上。等到秧苗呼啦啦长得发绿,田埂上便浅浅地生出了蚕豆几瓣嫩嫩的绿叶,像是春天的两只耳朵在风中摇摆,倾听着水田里秧苗发棵拔节的声音。
很快,它们就像一对相依相偎的小儿女——别看蚕豆的叶片是绿色的,秧苗也是绿色的,它们都绿得有些天真烂漫,但随着绿色的秧苗撒欢般长高了个子,蚕豆的叶片在田埂上就随风一溜开跑,跑了几趟,蚕豆就开出淡紫色的花了。在这之前,稻田里有水,水像一汪明镜似地倒映着明月,蓝蓝的天空、朝霞和夕阳,偶尔还有一只翠鸟飞过——那些刚栽插下去的秧苗,是在另一块田里生根发芽,被人小心移植过来的。它从种子落地的那天起就离不开水,而蚕豆就不一样,它只被人丢在田埂的泥宕里,遇土生根发芽,漠漠青田白鹭飞时,它还没有冒出头来,但等田里的秧苗长成水稻,它却灿烂如霞。在这时候,人们才像分辨男孩女孩一样分辨出它们各自的品质来。
终是要收获的。到收获时,男人收割稻子,女人收获蚕豆。“春丢一粒籽,夏发万棵芽,咿子呀子哟……”她们头裹蓝色的头巾,嘴里哼着黄梅调,手舞足蹈,低身弯腰就收拾了起来。这时蚕豆紫色的花瓣已开始凋谢,但那根茎却结着粒粒饱满的荚果——蚕豆。蚕豆在花的凋谢声中大声喊着自己的名字,那脆亮的名字就从绿色的根茎上滴落下来,青青的,青得像一块绿宝石,青得惹人怜爱。这样品质优良的蚕豆是可以留作种子的,乡亲们往往选上一些,放进一个布袋里吊在房梁上。有一年春荒时,趁母亲不在家,我发现了那只布袋的秘密,不知怎么我打开布袋就把那蚕豆种子偷偷炒着吃了。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母亲知道后,不停地责备我:“你这伢,你这伢……”不知说什么才好。现在,乡亲们种蚕豆是一种心情,吃蚕豆也是一种心情。她们把那青青的蚕豆在水里认真地洗净,放在锅里,伴着鸡蛋就能烧出一锅美味来。淡黄的鸡蛋,清清的汤水漾着绿色的豆,喝进嘴里鲜美无比,蚕豆粉团团地嚼在舌尖上,更是颊齿留香——新鲜的蚕豆一时吃不完,乡亲们就用竹器盛着放在太阳下晒,然后烧红锅在锅里炒,那蚕豆在红红的锅里活蹦乱跳的,隔着几里路外都能闻到蚕豆浓浓的香味。炒好的蚕豆冷却一下,吃在嘴里嘎嘣干脆,青香沁人肺腑。逢年过节的,乡亲们用这招待客人,尤其是小孩子,刚好可以试试一个人牙齿的硬度与韧性。这时候男人们要是出门干重重的农活,比如担一担稻草什么的,你抓一把蚕豆给他,他便一路走一路吃着,再去挑那担子就显得轻松多了。
水稻成熟时是金黄色的,浑身每一缕肌肤都泛着铜一样的光芒。金黄直达它的根部,也抵达乡亲们的心灵。而蚕豆则不是,它的根茎是方形,中心空,细看那花是洁白的,紫色只是那白色中的斑痕,如一方白纱巾不小心沾了紫的颜料。稻子在水田里灌浆、扬花,也因为水,它的呼吸舒畅而粗重,而蚕豆的呼吸却很微弱。水稻越长越是粗壮,也更高大些,而蚕豆却将紫花紧紧贴着地面,低低的,低得似乎要低到尘埃里去,如一位腼腆害羞的少女,不敢抬头看着面前的男人,却将头紧紧地倚靠在男人的胸脯上——这与它知道它和水稻的处境不同似乎也很有关系。水稻是中国的粮食,是南方人须臾不可缺少的大面积收获和大面积填饱肚子的物质,但它啥也不是,充其量只是乡亲们过年过节用来调味的食物。水稻是男性的,她是雌性的,她生来就是乡野人家的小女儿。看看,金黄色的稻田周围盛开的蚕豆花,把稻田从青转黄都镶上了一道紫色的花边。早晨的时候,乡亲们赤脚走在田埂上,双脚踩着那带着重重露水的蚕豆花,就像踩着一片云,那偶尔沾在裤脚上的紫色花瓣,仿佛小女孩一路不停地笑。
蚕豆开花是紫色。
那是一种无边无际蔓延的,浅浅地带有几分忧郁的紫。那紫色的笑,听了都叫人心颤。

徐迅 著有小说集《某月某日寻访不遇》,散文集《徐迅散文年编(4卷)》(《雪原无边》《皖河散记》《鲜亮的雨》《秋山响水》)、《半堵墙》《响水在溪——名家散文自选集》等20部。曾获首届老舍散文奖、第二届冰心散文奖、三毛散文奖、十月琦君散文奖、乌金文学奖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优秀作品等。现任中国煤矿文联副主席、中国煤矿作协常务副主席,系中国作协第九、十届全委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

珠海传媒集团 吴长赋摄
□ 卢一萍
光雾山有险峻之美,但秀美居多,即使是险,也险得有秀美之气。我徒步登过两次香炉峰,不过已是木质步道,很好行走,上到峰顶,并不吃力。现在有了索道,即使我年已八十岁的母亲也可登顶游览了,这也未尝不是好事。
香炉峰自大坝河边,自河岸边的丛林处拔地而起,高耸如云。但其南坡开始并不陡峭,直到半山,才壁立起来;而北坡则几乎是从深谷的最底处陡然而起的,即使一片落叶,也似乎可以飘到谷底。
到大坝,这个曾经与世隔绝、有点桃花源意味的地方,现在很多居民已经迁出,只有那几户临河而居的人家因在这里开旅舍、农家乐,还住在这里。大多数田地已被森林占据,绿树密匝,人已很难进去。四周绿色的山岭并不高拔,山形弧线优美,坡度缓和,容易亲近。一条双向两车道的柏油路在谷底蜿蜒,车行其中,都是在林海中穿越。
从牟阳城遗址行不多远,便进入一片落叶松林。每一棵树都长得笔直,成行成排,如接受检阅的中国士兵。树干溜光,都自然裸露到了统一的高度,显得很是性感。树下则开满了一种紫色的花,松树的香气与花香混合在一起,被林风送来,令人有一种轻微的陶醉感。车穿过这样一片森林,显得很是浪费;可步行期间,又觉得奢侈。
就是这一处风景,都显得如此盛大。而这种盛大来自那些微小的东西:松风、鸟鸣、落叶触地之声、河水撞击卵石的回音,脚踩在落叶上、泥土上的轻微的弹力,阳光透过密密的叶隙,如线如缕地照射到开满花的林地上,大小不一的光斑在风吹动树林时,也会随摇曳的光线而来回移动……而我又一直沉浸在森林的气息里,最主要的是,我可以一直大口地、无所顾忌地呼吸,我可以感觉到空气进入肺腑时那股香甜的味道。
落叶松林富有诗意地往前延伸,我们得中途转往索道站。一道被犁出的沟壕从山脚一直延伸到接近山顶的地方,显得有些丑陋,像一个美人的一头秀发被人推了一剪子,露出了头皮。任何现代化的设施在这样的地方都显得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它无疑是天然之美和人类古老诗意的反面。但这可以方便游客去往香炉山顶。当然,这样一个设施也有可能赚钱。
下了索道,就是木质步行道。路的两边都是风景,一步一景,各不相同。香炉峰顶的确是奇景所在,它是由一个庞大的喀斯特峰丛构成的高处的园林——每一个细节都可谓鬼斧神工。给人的感觉是,它的确像某位神仙在这里私造的仙境。特别是有云雾的时候,峰丛时隐时现,实在,又虚幻、缥缈,树木悬空而生,枝丫伸出悬崖很远。古柏——也就是巴山崖柏、杜鹃向死而生,崖柏苍劲、虬曲,但生命常绿,有了难得一见的生命姿态,那就是永不向这个世界的严酷低头,它一年也许只能生长零点零一毫米,但它可以用一万年的时间来生长——似乎连一株草都经历了千年岁月的风吹雨打、冰冻霜寒。高山杜鹃似乎因为叫了这个名字,也就不恐高,多临渊而生。这种植物我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见过,它们伏地而生,格外葳蕤繁茂。经历半年甚至七八个月冰雪碾压,即使天气和缓,中午阳光灿烂,晚上又是霜冻冰裹,但该开花的时候,依然迎寒怒放,在冰峰雪岭的映照下,整个天地都显得无比辉煌。我曾面对那般美景,半晌无语,却泪如泉涌。没有想到,在我故乡的高山之上,我也见到了它。它们也长得恣肆,因多生于悬崖峭壁,很多只能让枝叶横逸,似乎风一吹,就会跌落深涧。
我想象,它们的一粒种子落在岩壁上的一处缝隙或一个拳头大小的石窝里,那里有一点不知风在何年吹来后积攒下的尘土,甚至那里原来仅一斑苔藓,靠着冰雪或雨水的滋润,发了芽,慢慢生长,把根扎进石缝深处,把小石窝撑满,然后用根浸蚀,让石头一点点变软,同时让自己偶尔掉落在那里的三四片落叶化为土,五六枚落花化为泥,成为养分,然后把根须伸出去,趁着夏日岩壁的潮湿,把根扎向其他地方;落在苔藓上的种子的根也是随着苔藓的蔓延,把根系向四周蔓延开去,最后抓住了岩石,生长起来。
其实,不仅是杜鹃,崖柏也是,这上面所有的植物都是。这也就是植物的伟大所在。没有它们如此坚韧顽强的生命力,就没有香炉峰顶的美,就没有这高处的仙境。我最后算是明白了,所谓的神仙,就是大自然本身——也只有它的无穷伟力才可创造一切,成就一切。
香炉峰在川东北的苍茫群山中,的确是高拔的,四五月间,有时甚至六月间,都有飞雪。它的确是险峻的,有些地方,之前人根本不可能去,现在,通过人工架设了木头栈道,有些地方挂在峭壁之上,有些架在两峰之间,凌空高悬,行走其上,既令人双腿战栗,又很是刺激。
香炉峰顶是最佳的登高地,也是最好的远望处。如遇晴日,汉中平原可一览无余。
站在峰顶,极目四望,四周都是由层层青山汇聚而成的绿色大海,直到天际,起伏不定,波涛汹涌,似乎可以听见绿色的浪涛声。我如同置身于香炉峰这个至美的孤岛上,茫茫的大海没有边际,令人感到自己与这个世界失去了联系,竟觉得有点孤独,不由生起一种淡淡的伤感来。
光雾山无疑是整列大巴山脉经典的、具有代表性的风景之一,而香炉峰展现了光雾山卓越的风骨,山风、云海、雾气、绿树、溪水、花果和飞禽走兽,将山变活,有了舞蹈之姿。

卢一萍 当代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白山》《我的绝代佳人》,小说集《银绳般的雪》《天堂湾》《帕米尔情歌》《大震》,长篇纪实文学《八千湘女上天山》《扶贫志》。作品曾获解放军文艺奖、中国报告文学大奖、“五个一”工程奖等。《白山》曾被评为“亚洲周刊2017年十大小说”。
□ 安武林

珠海传媒集团 刘轶男摄
美食的诱惑,世人是很难抵御的。君不见任何一个朋友的聚会上,总有一些吃相很难看的人。他们眼睛只盯着美味佳肴,旁若无人的样子,犹如书痴在聚精会神地阅读一样。其实,吃相难看的人,在我看来是美食的使者,和天使一样的可爱。他们和性情中人一样,只不过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性情而已。这是对美食的讴歌和赞美,发自心灵,途经肠胃。那些矜持的人,倒不是什么修养好,也算不得高明,更不用贴什么绅士和淑女的标签。在个人私见,那不过是文明所使用的一种修辞方法而已。涂掉诚实,抹掉虚伪,留下闪闪发光的两个字:修养。
美食的诱惑力到底有多大?不太好衡量。但有一篇文章,倒是很好的例证。它如同实验室里的数据一样,基本诚实可靠。那就是都德《磨坊书简》里的《三遍小弥撒》。如果抛开形而上的大主题之外,我们会发现它的小主题就是美食的诱惑。美食到底多有杀伤力?一个魔鬼扮做一个合唱班的小队员加里古,来考验巴拉格尔牧师,考验牧师是否能抵制住美食的诱惑。
《三遍小弥撒》开始的第一句,是巴拉格尔牧师的问话,他在问魔鬼装扮成的合唱班的小队员加里古。牧师的问话给人无穷的联想,至少,在作者省略的内容里,我们能看出来加里古已经打开了美食的魔瓶。牧师闪闪发亮的眼睛,咽唾沫的声音,喉结的蠕动,这些画面形象而又生动地浮现在我们面前。从两只香菇火鸡开始,牧师的想象力开始飞扬了。厨房里还有什么?牧师迫切想知道。魔鬼就是魔鬼,知道美食的无穷的魅力。加里古说“应有尽有!”嘿,野鸡,戴胜,松鸡,大松鸡,黄鳝,金色鲤鱼和白鲈鱼……加里古,鲈鱼有多大?有这么大,尊敬的牧师……大得很啊……天哪,我好像看见了……得,牧师真正变成了一条鱼,他被魔鬼加里古紧紧地钓住了。
当当当,魔鬼加里古敲响了钟声。
牧师一边穿衣服,一边念叨着:“好多火熏鸡……好多金鲤鱼……还有好多这么粗的黄鳝啊!”
牧师心慌意乱,开始节节败退。保持矜持,保持节制,保持坚定,这是一个牧师所需要的基本元素,可是,巴拉格尔牧师早已经抛弃它们了。他的眼里只有美食的影子,气味,心里不断念叨和盼望着早点结束。
在做第二遍弥撒的时候,牧师心里只有一个字“快快快!”他恨不得省去所有的繁文缛节,立刻结束。他在弥撒经上奔跑,似乎和歌童比赛谁朗诵得快一样。叽里咕噜,恐怕自己都听不明白了。谢天谢地,第二遍弥撒结束,牧师脸红了,冒汗了。
第三遍弥撒开始,牧师已经出现了幻觉,美食的诱惑力像大雾一样笼罩着牧师的视野。目力所及,尽是美食,一道一道从他眼前飘过,像是在接受他的检阅一样。牧师混乱了,开始跳读了,人们已经跟不上他的节奏了,也不知道已经读到哪儿了。人们随着牧师的手势和动作来判断内容。一些人站起来了,一些人坐下去了,此起彼伏,混乱不堪。而弹钢琴的阿尔诺东先生戴着眼镜不断在祷告书上搜寻牧师读到哪儿了。只有一个老妇人,咕哝出了真相:“神父跑得太快了……大家跟不上。”
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传说,都德用生花的妙笔栩栩如生地描写了出来。虽然说加里古是个魔鬼,但却没有使用我们日常阅读的那些魔幻故事中的魔法,他只不过借助美食的诱惑,考验了一把牧师。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美食的诱惑力到底有多大?读读都德的《三遍小弥撒》就一清二楚了,牧师投降了,失败了,不过,这不算什么丢人的。美食无罪,爱美食也无罪。

安武林 儿童文学作家,诗人,评论家。出版过小说《泥巴男生》、散文集《黑豆里的母亲》、散文诗集《星星的秋千》、童话集《老蜘蛛的一百张床》、诗集《月光下的蝈蝈》等三百余种作品集。荣获过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张天翼童话金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文化部蒲公英儿童文学奖等。作品被翻译到美国、斯里兰卡、英国、摩洛哥等国家。
春风来信
(外一首)
□ 阿 翔

珠海传媒集团 刘轶男摄
天性的颤音会集中于比更多的风声
还要活泼,仿佛有很多的东西
它无关时间的涂抹是否依赖于
一封信成为时间本身最暧昧的迟疑;
当你代替我,它就是风铃的乐观主义,
仅凭纯粹的气氛就能沉淀
纯粹的幽暗;甚至自然的动静
来自风景的口味,令翡翠像治愈
抑郁症的偏方。至于起伏之间,
它偏爱湍急的水流在我们中间追逐
一点不像陪衬里需要任何理由。
而你愿意相信比起高大的木棉,春天的
凤凰木更合适它的寂静之舞,
直到它的飞翔在源头方向只剩下一口气;
怎么扎根,似乎取决于它在自我的
挖掘中怎么成长,这意味着也是
不曾误解过的一种时光秘密。
只要我们能看懂世界是一个不受限于
人的视野,甚至深刻于蝴蝶的影子,
也是可能的。
如果你不曾估算一首赞美诗
被减轻了花蕊的分量,那么新枝上的
新芽又如何兜底一场雨还会有后门。
或者退一步,这么好的清晰悦耳,
而且来自比神奇更神秘的天籁之音,
置身于巨大的现实,任何轻微能决定
自然的深处围绕着它起舞,就好像
我们的灵魂也可以得以轻盈。
清明来信
它最好来自细雨中消失的蝴蝶,
很少有人会像你那样留意过
一个绽放的象征性远远低于湖畔中央。
我们已经习惯生活中的忍耐力,
没背叛过虚无的人,就不会有兴趣了解
风俗的死角仿佛比天堂还干净。
它最好是死者使用过的语言中
有一个浩瀚的走神;凭这唯一的交流,
它把绿荫和春天的疤斑分别交给你。
不同于深邃,它近乎自然的迹象意味着
在你的孤独中得到一个新的定义,
纯粹的印象加深了短暂的美。
它最好没有成为一个热点,甚至
现实也挣脱了隐喻,甚至你才会先于我
认出它身上的另一个你。
它最好无关正式的仪式不全是消极的,
春风把你吹到樱花的舞蹈里,
鸢尾花在你的呼吸中蓝了又蓝。
它最好能随时感觉到你的脚步,
从未耽误过我们神秘的信赖,
大地的祭坛,至少涉及过最后的慰藉。


阿翔 生于1970年,1986年写作至今。著有《少年诗》《一切流逝完好如初》《一首诗的战栗》《旧叙事与星辰造梦师》等诗集。现居深圳。



□ 徐 迅

图源:新华社
春丢一粒籽,夏发万棵芽,咿子呀子哟……黄梅小调唱得好像就是蚕豆。很多年以来,蚕豆就是这样生长在南方的田间地头。乡亲们仿佛知道蚕豆有很强的生命力,很少大面积种植,而是漫不经心地在插完秧后,顺手一溜地撒落在田埂上。等到秧苗呼啦啦长得发绿,田埂上便浅浅地生出了蚕豆几瓣嫩嫩的绿叶,像是春天的两只耳朵在风中摇摆,倾听着水田里秧苗发棵拔节的声音。
很快,它们就像一对相依相偎的小儿女——别看蚕豆的叶片是绿色的,秧苗也是绿色的,它们都绿得有些天真烂漫,但随着绿色的秧苗撒欢般长高了个子,蚕豆的叶片在田埂上就随风一溜开跑,跑了几趟,蚕豆就开出淡紫色的花了。在这之前,稻田里有水,水像一汪明镜似地倒映着明月,蓝蓝的天空、朝霞和夕阳,偶尔还有一只翠鸟飞过——那些刚栽插下去的秧苗,是在另一块田里生根发芽,被人小心移植过来的。它从种子落地的那天起就离不开水,而蚕豆就不一样,它只被人丢在田埂的泥宕里,遇土生根发芽,漠漠青田白鹭飞时,它还没有冒出头来,但等田里的秧苗长成水稻,它却灿烂如霞。在这时候,人们才像分辨男孩女孩一样分辨出它们各自的品质来。
终是要收获的。到收获时,男人收割稻子,女人收获蚕豆。“春丢一粒籽,夏发万棵芽,咿子呀子哟……”她们头裹蓝色的头巾,嘴里哼着黄梅调,手舞足蹈,低身弯腰就收拾了起来。这时蚕豆紫色的花瓣已开始凋谢,但那根茎却结着粒粒饱满的荚果——蚕豆。蚕豆在花的凋谢声中大声喊着自己的名字,那脆亮的名字就从绿色的根茎上滴落下来,青青的,青得像一块绿宝石,青得惹人怜爱。这样品质优良的蚕豆是可以留作种子的,乡亲们往往选上一些,放进一个布袋里吊在房梁上。有一年春荒时,趁母亲不在家,我发现了那只布袋的秘密,不知怎么我打开布袋就把那蚕豆种子偷偷炒着吃了。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母亲知道后,不停地责备我:“你这伢,你这伢……”不知说什么才好。现在,乡亲们种蚕豆是一种心情,吃蚕豆也是一种心情。她们把那青青的蚕豆在水里认真地洗净,放在锅里,伴着鸡蛋就能烧出一锅美味来。淡黄的鸡蛋,清清的汤水漾着绿色的豆,喝进嘴里鲜美无比,蚕豆粉团团地嚼在舌尖上,更是颊齿留香——新鲜的蚕豆一时吃不完,乡亲们就用竹器盛着放在太阳下晒,然后烧红锅在锅里炒,那蚕豆在红红的锅里活蹦乱跳的,隔着几里路外都能闻到蚕豆浓浓的香味。炒好的蚕豆冷却一下,吃在嘴里嘎嘣干脆,青香沁人肺腑。逢年过节的,乡亲们用这招待客人,尤其是小孩子,刚好可以试试一个人牙齿的硬度与韧性。这时候男人们要是出门干重重的农活,比如担一担稻草什么的,你抓一把蚕豆给他,他便一路走一路吃着,再去挑那担子就显得轻松多了。
水稻成熟时是金黄色的,浑身每一缕肌肤都泛着铜一样的光芒。金黄直达它的根部,也抵达乡亲们的心灵。而蚕豆则不是,它的根茎是方形,中心空,细看那花是洁白的,紫色只是那白色中的斑痕,如一方白纱巾不小心沾了紫的颜料。稻子在水田里灌浆、扬花,也因为水,它的呼吸舒畅而粗重,而蚕豆的呼吸却很微弱。水稻越长越是粗壮,也更高大些,而蚕豆却将紫花紧紧贴着地面,低低的,低得似乎要低到尘埃里去,如一位腼腆害羞的少女,不敢抬头看着面前的男人,却将头紧紧地倚靠在男人的胸脯上——这与它知道它和水稻的处境不同似乎也很有关系。水稻是中国的粮食,是南方人须臾不可缺少的大面积收获和大面积填饱肚子的物质,但它啥也不是,充其量只是乡亲们过年过节用来调味的食物。水稻是男性的,她是雌性的,她生来就是乡野人家的小女儿。看看,金黄色的稻田周围盛开的蚕豆花,把稻田从青转黄都镶上了一道紫色的花边。早晨的时候,乡亲们赤脚走在田埂上,双脚踩着那带着重重露水的蚕豆花,就像踩着一片云,那偶尔沾在裤脚上的紫色花瓣,仿佛小女孩一路不停地笑。
蚕豆开花是紫色。
那是一种无边无际蔓延的,浅浅地带有几分忧郁的紫。那紫色的笑,听了都叫人心颤。

徐迅 著有小说集《某月某日寻访不遇》,散文集《徐迅散文年编(4卷)》(《雪原无边》《皖河散记》《鲜亮的雨》《秋山响水》)、《半堵墙》《响水在溪——名家散文自选集》等20部。曾获首届老舍散文奖、第二届冰心散文奖、三毛散文奖、十月琦君散文奖、乌金文学奖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优秀作品等。现任中国煤矿文联副主席、中国煤矿作协常务副主席,系中国作协第九、十届全委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

珠海传媒集团 吴长赋摄
□ 卢一萍
光雾山有险峻之美,但秀美居多,即使是险,也险得有秀美之气。我徒步登过两次香炉峰,不过已是木质步道,很好行走,上到峰顶,并不吃力。现在有了索道,即使我年已八十岁的母亲也可登顶游览了,这也未尝不是好事。
香炉峰自大坝河边,自河岸边的丛林处拔地而起,高耸如云。但其南坡开始并不陡峭,直到半山,才壁立起来;而北坡则几乎是从深谷的最底处陡然而起的,即使一片落叶,也似乎可以飘到谷底。
到大坝,这个曾经与世隔绝、有点桃花源意味的地方,现在很多居民已经迁出,只有那几户临河而居的人家因在这里开旅舍、农家乐,还住在这里。大多数田地已被森林占据,绿树密匝,人已很难进去。四周绿色的山岭并不高拔,山形弧线优美,坡度缓和,容易亲近。一条双向两车道的柏油路在谷底蜿蜒,车行其中,都是在林海中穿越。
从牟阳城遗址行不多远,便进入一片落叶松林。每一棵树都长得笔直,成行成排,如接受检阅的中国士兵。树干溜光,都自然裸露到了统一的高度,显得很是性感。树下则开满了一种紫色的花,松树的香气与花香混合在一起,被林风送来,令人有一种轻微的陶醉感。车穿过这样一片森林,显得很是浪费;可步行期间,又觉得奢侈。
就是这一处风景,都显得如此盛大。而这种盛大来自那些微小的东西:松风、鸟鸣、落叶触地之声、河水撞击卵石的回音,脚踩在落叶上、泥土上的轻微的弹力,阳光透过密密的叶隙,如线如缕地照射到开满花的林地上,大小不一的光斑在风吹动树林时,也会随摇曳的光线而来回移动……而我又一直沉浸在森林的气息里,最主要的是,我可以一直大口地、无所顾忌地呼吸,我可以感觉到空气进入肺腑时那股香甜的味道。
落叶松林富有诗意地往前延伸,我们得中途转往索道站。一道被犁出的沟壕从山脚一直延伸到接近山顶的地方,显得有些丑陋,像一个美人的一头秀发被人推了一剪子,露出了头皮。任何现代化的设施在这样的地方都显得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它无疑是天然之美和人类古老诗意的反面。但这可以方便游客去往香炉山顶。当然,这样一个设施也有可能赚钱。
下了索道,就是木质步行道。路的两边都是风景,一步一景,各不相同。香炉峰顶的确是奇景所在,它是由一个庞大的喀斯特峰丛构成的高处的园林——每一个细节都可谓鬼斧神工。给人的感觉是,它的确像某位神仙在这里私造的仙境。特别是有云雾的时候,峰丛时隐时现,实在,又虚幻、缥缈,树木悬空而生,枝丫伸出悬崖很远。古柏——也就是巴山崖柏、杜鹃向死而生,崖柏苍劲、虬曲,但生命常绿,有了难得一见的生命姿态,那就是永不向这个世界的严酷低头,它一年也许只能生长零点零一毫米,但它可以用一万年的时间来生长——似乎连一株草都经历了千年岁月的风吹雨打、冰冻霜寒。高山杜鹃似乎因为叫了这个名字,也就不恐高,多临渊而生。这种植物我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见过,它们伏地而生,格外葳蕤繁茂。经历半年甚至七八个月冰雪碾压,即使天气和缓,中午阳光灿烂,晚上又是霜冻冰裹,但该开花的时候,依然迎寒怒放,在冰峰雪岭的映照下,整个天地都显得无比辉煌。我曾面对那般美景,半晌无语,却泪如泉涌。没有想到,在我故乡的高山之上,我也见到了它。它们也长得恣肆,因多生于悬崖峭壁,很多只能让枝叶横逸,似乎风一吹,就会跌落深涧。
我想象,它们的一粒种子落在岩壁上的一处缝隙或一个拳头大小的石窝里,那里有一点不知风在何年吹来后积攒下的尘土,甚至那里原来仅一斑苔藓,靠着冰雪或雨水的滋润,发了芽,慢慢生长,把根扎进石缝深处,把小石窝撑满,然后用根浸蚀,让石头一点点变软,同时让自己偶尔掉落在那里的三四片落叶化为土,五六枚落花化为泥,成为养分,然后把根须伸出去,趁着夏日岩壁的潮湿,把根扎向其他地方;落在苔藓上的种子的根也是随着苔藓的蔓延,把根系向四周蔓延开去,最后抓住了岩石,生长起来。
其实,不仅是杜鹃,崖柏也是,这上面所有的植物都是。这也就是植物的伟大所在。没有它们如此坚韧顽强的生命力,就没有香炉峰顶的美,就没有这高处的仙境。我最后算是明白了,所谓的神仙,就是大自然本身——也只有它的无穷伟力才可创造一切,成就一切。
香炉峰在川东北的苍茫群山中,的确是高拔的,四五月间,有时甚至六月间,都有飞雪。它的确是险峻的,有些地方,之前人根本不可能去,现在,通过人工架设了木头栈道,有些地方挂在峭壁之上,有些架在两峰之间,凌空高悬,行走其上,既令人双腿战栗,又很是刺激。
香炉峰顶是最佳的登高地,也是最好的远望处。如遇晴日,汉中平原可一览无余。
站在峰顶,极目四望,四周都是由层层青山汇聚而成的绿色大海,直到天际,起伏不定,波涛汹涌,似乎可以听见绿色的浪涛声。我如同置身于香炉峰这个至美的孤岛上,茫茫的大海没有边际,令人感到自己与这个世界失去了联系,竟觉得有点孤独,不由生起一种淡淡的伤感来。
光雾山无疑是整列大巴山脉经典的、具有代表性的风景之一,而香炉峰展现了光雾山卓越的风骨,山风、云海、雾气、绿树、溪水、花果和飞禽走兽,将山变活,有了舞蹈之姿。

卢一萍 当代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白山》《我的绝代佳人》,小说集《银绳般的雪》《天堂湾》《帕米尔情歌》《大震》,长篇纪实文学《八千湘女上天山》《扶贫志》。作品曾获解放军文艺奖、中国报告文学大奖、“五个一”工程奖等。《白山》曾被评为“亚洲周刊2017年十大小说”。
□ 安武林

珠海传媒集团 刘轶男摄
美食的诱惑,世人是很难抵御的。君不见任何一个朋友的聚会上,总有一些吃相很难看的人。他们眼睛只盯着美味佳肴,旁若无人的样子,犹如书痴在聚精会神地阅读一样。其实,吃相难看的人,在我看来是美食的使者,和天使一样的可爱。他们和性情中人一样,只不过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性情而已。这是对美食的讴歌和赞美,发自心灵,途经肠胃。那些矜持的人,倒不是什么修养好,也算不得高明,更不用贴什么绅士和淑女的标签。在个人私见,那不过是文明所使用的一种修辞方法而已。涂掉诚实,抹掉虚伪,留下闪闪发光的两个字:修养。
美食的诱惑力到底有多大?不太好衡量。但有一篇文章,倒是很好的例证。它如同实验室里的数据一样,基本诚实可靠。那就是都德《磨坊书简》里的《三遍小弥撒》。如果抛开形而上的大主题之外,我们会发现它的小主题就是美食的诱惑。美食到底多有杀伤力?一个魔鬼扮做一个合唱班的小队员加里古,来考验巴拉格尔牧师,考验牧师是否能抵制住美食的诱惑。
《三遍小弥撒》开始的第一句,是巴拉格尔牧师的问话,他在问魔鬼装扮成的合唱班的小队员加里古。牧师的问话给人无穷的联想,至少,在作者省略的内容里,我们能看出来加里古已经打开了美食的魔瓶。牧师闪闪发亮的眼睛,咽唾沫的声音,喉结的蠕动,这些画面形象而又生动地浮现在我们面前。从两只香菇火鸡开始,牧师的想象力开始飞扬了。厨房里还有什么?牧师迫切想知道。魔鬼就是魔鬼,知道美食的无穷的魅力。加里古说“应有尽有!”嘿,野鸡,戴胜,松鸡,大松鸡,黄鳝,金色鲤鱼和白鲈鱼……加里古,鲈鱼有多大?有这么大,尊敬的牧师……大得很啊……天哪,我好像看见了……得,牧师真正变成了一条鱼,他被魔鬼加里古紧紧地钓住了。
当当当,魔鬼加里古敲响了钟声。
牧师一边穿衣服,一边念叨着:“好多火熏鸡……好多金鲤鱼……还有好多这么粗的黄鳝啊!”
牧师心慌意乱,开始节节败退。保持矜持,保持节制,保持坚定,这是一个牧师所需要的基本元素,可是,巴拉格尔牧师早已经抛弃它们了。他的眼里只有美食的影子,气味,心里不断念叨和盼望着早点结束。
在做第二遍弥撒的时候,牧师心里只有一个字“快快快!”他恨不得省去所有的繁文缛节,立刻结束。他在弥撒经上奔跑,似乎和歌童比赛谁朗诵得快一样。叽里咕噜,恐怕自己都听不明白了。谢天谢地,第二遍弥撒结束,牧师脸红了,冒汗了。
第三遍弥撒开始,牧师已经出现了幻觉,美食的诱惑力像大雾一样笼罩着牧师的视野。目力所及,尽是美食,一道一道从他眼前飘过,像是在接受他的检阅一样。牧师混乱了,开始跳读了,人们已经跟不上他的节奏了,也不知道已经读到哪儿了。人们随着牧师的手势和动作来判断内容。一些人站起来了,一些人坐下去了,此起彼伏,混乱不堪。而弹钢琴的阿尔诺东先生戴着眼镜不断在祷告书上搜寻牧师读到哪儿了。只有一个老妇人,咕哝出了真相:“神父跑得太快了……大家跟不上。”
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传说,都德用生花的妙笔栩栩如生地描写了出来。虽然说加里古是个魔鬼,但却没有使用我们日常阅读的那些魔幻故事中的魔法,他只不过借助美食的诱惑,考验了一把牧师。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美食的诱惑力到底有多大?读读都德的《三遍小弥撒》就一清二楚了,牧师投降了,失败了,不过,这不算什么丢人的。美食无罪,爱美食也无罪。

安武林 儿童文学作家,诗人,评论家。出版过小说《泥巴男生》、散文集《黑豆里的母亲》、散文诗集《星星的秋千》、童话集《老蜘蛛的一百张床》、诗集《月光下的蝈蝈》等三百余种作品集。荣获过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张天翼童话金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文化部蒲公英儿童文学奖等。作品被翻译到美国、斯里兰卡、英国、摩洛哥等国家。
春风来信
(外一首)
□ 阿 翔

珠海传媒集团 刘轶男摄
天性的颤音会集中于比更多的风声
还要活泼,仿佛有很多的东西
它无关时间的涂抹是否依赖于
一封信成为时间本身最暧昧的迟疑;
当你代替我,它就是风铃的乐观主义,
仅凭纯粹的气氛就能沉淀
纯粹的幽暗;甚至自然的动静
来自风景的口味,令翡翠像治愈
抑郁症的偏方。至于起伏之间,
它偏爱湍急的水流在我们中间追逐
一点不像陪衬里需要任何理由。
而你愿意相信比起高大的木棉,春天的
凤凰木更合适它的寂静之舞,
直到它的飞翔在源头方向只剩下一口气;
怎么扎根,似乎取决于它在自我的
挖掘中怎么成长,这意味着也是
不曾误解过的一种时光秘密。
只要我们能看懂世界是一个不受限于
人的视野,甚至深刻于蝴蝶的影子,
也是可能的。
如果你不曾估算一首赞美诗
被减轻了花蕊的分量,那么新枝上的
新芽又如何兜底一场雨还会有后门。
或者退一步,这么好的清晰悦耳,
而且来自比神奇更神秘的天籁之音,
置身于巨大的现实,任何轻微能决定
自然的深处围绕着它起舞,就好像
我们的灵魂也可以得以轻盈。
清明来信
它最好来自细雨中消失的蝴蝶,
很少有人会像你那样留意过
一个绽放的象征性远远低于湖畔中央。
我们已经习惯生活中的忍耐力,
没背叛过虚无的人,就不会有兴趣了解
风俗的死角仿佛比天堂还干净。
它最好是死者使用过的语言中
有一个浩瀚的走神;凭这唯一的交流,
它把绿荫和春天的疤斑分别交给你。
不同于深邃,它近乎自然的迹象意味着
在你的孤独中得到一个新的定义,
纯粹的印象加深了短暂的美。
它最好没有成为一个热点,甚至
现实也挣脱了隐喻,甚至你才会先于我
认出它身上的另一个你。
它最好无关正式的仪式不全是消极的,
春风把你吹到樱花的舞蹈里,
鸢尾花在你的呼吸中蓝了又蓝。
它最好能随时感觉到你的脚步,
从未耽误过我们神秘的信赖,
大地的祭坛,至少涉及过最后的慰藉。


阿翔 生于1970年,1986年写作至今。著有《少年诗》《一切流逝完好如初》《一首诗的战栗》《旧叙事与星辰造梦师》等诗集。现居深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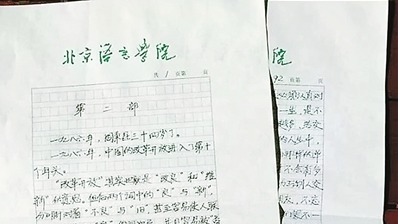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