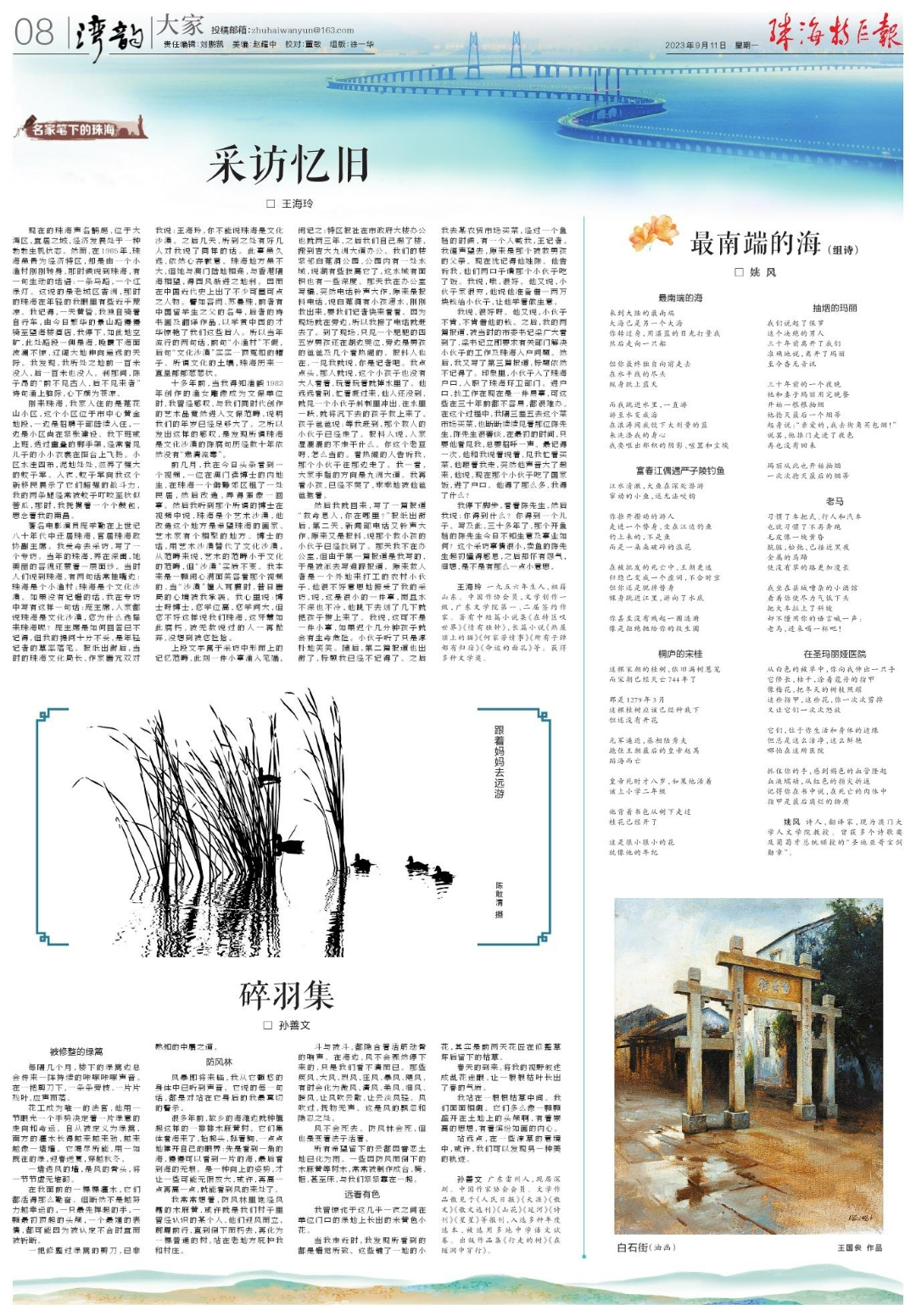
□王海玲

现在的珠海声名鹊起,位于大湾区,宜居之城,经济发展处于一种勃勃生机状态。然而,在1985年,珠海虽贵为经济特区,却是由一个小渔村刚刚转身,那时候说到珠海,有一句生动的话语:一条马路,一个红绿灯。这说的是老城区香洲,那时的珠海在年轻的我眼里有些近乎荒凉。我记得,一天黄昏,我独自骑着自行车,由今日繁华的景山路慢慢骑至望海楼酒店,我停下,如此地空旷,此处路段一侧是海,晚霞下海面波澜不惊,辽阔大地伸向遥远的天际。我发现,我所处之地前一百米没人,后一百米也没人。刹那间,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诗句涌上脑际,心下颇为苍凉。
刚来珠海,我家入住的是莲花山小区,这个小区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一边是招聘干部陆续入住,一边是小区尚在紧张建设。我下班或上班,透过重叠的脚手架,经常看见儿子的小小衣裳在阳台上飞扬。小区水洼四布,泥地处处,滋养了强大的蚊子军。入夜,蚊子军向我这个新移民展示了它们超强的战斗力,我的两条腿经常被蚊子叮咬至状似苦瓜,那时,我抚摸着一个个鼓包,思念着我的南昌。
著名电影演员庞学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迁居珠海,官居珠海政协副主席。我受命去采访,写了一个专访。当年的珠海,养在深闺,她美丽的容貌还蒙着一层面纱。当时人们说到珠海,有两句话常挂嘴边:珠海是个小渔村;珠海是个文化沙漠。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在专访中写有这样一句话:庞主席,人家都说珠海是文化沙漠,您为什么选择来珠海呢?庞主席是如何回答已不记得,但我的提问十分不妥,是年轻记者的草率落笔。报纸出街后,当时的珠海文化局长、作家唐亢双对我说:王海玲,你不能说珠海是文化沙漠。之后几天,所到之处有好几人对我说了同样的话。此事虽久远,依然心存歉意。珠海地方虽不大,但她与澳门陆地相连,与香港隔海相望,得西风渐进之地利。因而在中国近代史上出了不少可圈可点之人物。譬如容闳、苏曼殊,前者有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名号,后者的诗书画及翻译作品,以学贯中西的才华惊艳了我们这些后人。所以当年流行的两句话,前句“小渔村”不假,后句“文化沙漠”实实一顶冤扣的帽子。所谓文化的土壤,珠海历来一直呈郁郁葱葱状。
十多年前,当我得知潘鹤1982年创作的渔女雕像成为文保单位时,我曾经感叹,与我们同时代创作的艺术品竟然进入文保范畴,说明我们的年岁已经足够大了。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是发现所谓珠海是文化沙漠的陈腐句历经数十年依然没有“肃清流毒”。
前几月,我在今日头条看到一个视频,一位在澳门读博士的内地生,在珠海一个僻静郊区租了一处民居,然后改造,弄得蛮像一回事。然后我听到那个所谓的博士在视频中说,珠海是个艺术沙漠,他改造这个地方是希望珠海的画家、艺术家有个相聚的地方。博士的话,用艺术沙漠替代了文化沙漠,从范畴来说,艺术的范畴小于文化的范畴,但“沙漠”实质不变。我本来是一颗闲心满面笑容看那个视频的,当“沙漠”撞入耳膜时,昔日唐局的心境被我承袭。我心里说:博士呀博士,您学位高,您学问大,但您不好这样说我们珠海,这牙慧如此腐朽,被无数说过的人一再抛弃,没想到被您捡拾。
上段文字属于采访中形而上的记忆范畴,此刻一件小事涌入笔端,闲记之:特区报社在市政府大楼办公也就两三年,之后我们自己起了楼,搬到吉大九洲大道办公。我们的楼紧邻白莲洞公园,公园内有一处水域,说湖有些拔高它了,这水域有面积也有一些深度。那天我在办公室写稿,突然电话铃声大作,原来是报料电话,说白莲洞有小孩溺水,刚刚救出来,要我们记者快来看看。因为现场就在旁边,所以我接了电话就赶去了。到了现场,只见一个肥肥的四五岁男孩还在湖边哭泣,旁边是男孩的爸爸及几个看热闹的。报料人也在,一见我就说,你是记者吧。我点点头,那人就说,这个小孩子也没有大人看着,玩着玩着就掉水里了。他远远看到,忙着赶过来,他人还没到,就见一个小伙子斜刺里冲出,往水里一跃,就将沉下去的孩子救上来了。孩子爸爸说:等我赶到,那个救人的小伙子已经走了。报料人说,人家湿漉漉的不走干什么。你这个老豆呀,怎么当的。看热闹的人告诉我,那个小伙子往那边走了。我一看,大家手指的方向是九洲大道。我再看小孩,已经不哭了,乖乖地被他爸爸抱着。
然后我就回来,写了一篇报道“救命恩人,你在哪里?”报纸出街后,第二天,新闻部电话又铃声大作,原来又是报料,说那个救小孩的小伙子已经找到了。那天我不在办公室,但由于第一篇报道是我写的,于是被派去写追踪报道。原来救人者是一个外地来打工的农村小伙子,他很不好意思地接受了我的采访,说,这是很小的一件事,而且水不深也不冷,他跳下去划了几下就把孩子捞上来了。我说,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如果迟个几分钟孩子就会有生命危险。小伙子听了只是淳朴地笑笑。随后,第二篇报道也出街了,标题我已经不记得了。之后我去某农贸市场买菜,经过一个鱼档的时候,有一个人喊我,王记者。我循声望去,原来是那个被救男孩的父亲。现在犹记得他姓陈。他告诉我,他们两口子请那个小伙子吃了饭。我说,哦,很好。他又说,小伙子家很穷,他说他准备借一两万块钱给小伙子,让他学着做生意。
我说,很好呀。他又说,小伙子不肯,不肯借他的钱。之后,我的两篇报道,被当时的市委书记梁广大看到了,梁书记立即要求有关部门解决小伙子的工作及珠海入户问题。然后,我又写了第三篇报道,标题依然不记得了。印象里,小伙子入了珠海户口,入职了珠海环卫部门。进户口、找工作在现在是一件易事,可这些在三十年前都不容易,都很难办。在这个过程中,我隔三差五去这个菜市场买菜,也断断续续见着那位陈先生,陈先生很善谈,在最初的时间,只要他看见我,总要招呼一声。最记得一次,他和我说着说着,见我忙着买菜,他跟着我走,突然他声音大了起来,他说,现在那个小伙子吃了国家饭,进了户口。他得了那么多,我得了什么?
我停下脚步,看着陈先生,然后我说:你得到什么?你得到一个儿子。写及此,三十多年了,那个开鱼档的陈先生今日不知生意及事业如何?这个采访事情很小,卖鱼的陈先生起初懂得感恩,之后却怀有怨气,细想,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小意思。

王海玲 一九五六年生人,祖籍山东。中国作协会员,文学创作一级,广东文学院第一、二届签约作家。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在特区叹世界》《情有独钟》,长篇小说《热屋顶上的猫》《何家芳情事》《所有子弹都有归宿》《命运的面孔》等。获得多种文学奖。


跟着妈妈去远游。陈敢清 摄


□孙善文
被修整的绿篱
每隔几个月,楼下的绿篱边总会传来一阵持续的咔嚓咔嚓声音。在一把剪刀下,一条条旁枝、一片片残叶,应声而落。
花工成为唯一的法官,他用一节眼光一个手势决定着一片绿意的走向和命运。自从被定义为绿篱,南方的灌木长得越来越来劲,越来越像一堵墙。它竭尽所能,用一如既往的绿,迎春送夏,穿越秋冬。
一堵透风的墙,是风的骨头,将一节节虚无堆砌。
在我面前的一棵棵灌木,它们都活得那么勤奋。但断然不是越努力越幸运的,一只最先挥起的手,一颗最初顶起的头颅,一个最媚的表情,都可能因为被认定不合时宜而被斩断。
一把修整过绿篱的剪刀,已非熟知的中庸之道。
防风林
风暴即将来临,我从它颤悠的身体中已听到声音。它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站在它身后的我最真切的警示。
很多年前,故乡的海滩边就种植起这样的一排排木麻黄树。它们集体看海来了,抬起头,挺着胸,一点点地撑开自己的眼界:先是看到一角的海,慢慢可以看到一片的海,最后看到海的无垠。是一种向上的姿势,才让一些可能无限放大,或许,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就能看到风的来处了。
我常常想着,防风林里饱经风霜的木麻黄,或许就是我们村子里曾经认识的某个人,他们迎风而立,踯躅前行,直到倒下而朽去,再化为一棵普通的树,站在老地方庇护我和村庄。
斗与被斗,都隐含着活筋动骨的响声。在海边,风不会骤然停下来的,只是我们看不清而已。那些疾风、大风、烈风、狂风、暴风、飓风,有时会化为微风、清风、柔风、细风、暖风,让风吹云散,让云淡风轻。风吹过,抚物无声。这是风的飘忽和隐忍之处。
风不会死去。防风林会死,但也是变着法子活着。
所有希望留下的云都因眷恋土地已化为雨。一些因防风而倒下的木麻黄等树木,常常被制作成台、椅、柜,甚至床,与我们紧紧靠在一起。
远看有色
我曾惊诧于这几乎一夜之间在单位门口的绿地上长出的米黄色小花。
当我走近时,我发现所看到的都是错觉所致。这些铺了一地的小花,其实是前两天花匠在修整草坪后留下的枯草。
春天的到来,将我的视野叙述成乱花迷眼,让一根根枯叶长出了春的气质。
我站在一根根枯草中间。我们面面相觑。它们多么像一颗颗盛开在土地上的头颅啊,有着崇高的思想,有着缤纷如画的内心。
站远点,在一些潦草的意境中,或许,我们可以发现另一种美的轨迹。

孙善文 广东雷州人,现居深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天涯》《散文》《散文选刊》《山花》《延河》《诗刊》《星星》等报刊,入选多种年度选本,被选用多地中学语文试卷。出版作品集《行走的树》《在隧洞中穿行》。

白石街(油画)。王国俊 作品


□姚风

最南端的海
来到大陆的最南端
大海已是另一个大海
你转过身,用湛蓝的目光打量我
然后走向一只船
但你最终独自向前走去
在水平线的尽头
纵身跃上蓝天
而我跳进水里,一直游
游至水变成海
在浪涛间我饮下大剂量的蓝
来洗涤我的身心
我要呕出郁积的阴影、喧嚣和尘埃
富春江偶遇严子陵钓鱼
江水清澈,大鱼在深处潜游
窜动的小鱼,还无法咬钩
你推开攒动的游人
走进一个替身,坐在江边钓鱼
钓上来的,不是鱼
而是一朵朵破碎的浪花
在被批发的死亡中,王朝更迭
归隐已变成一个虚词,不合时宜
但你还是脱掉替身
裸身跳进江里,游向了水底
你甚至没有溅起一圈涟漪
像是拒绝抛给你的救生圈
桐庐的宋桂
这棵宋朝的桂树,依旧满树葱茏
而宋朝已经灭亡744年了
那是1279年3月
这棵桂树应该已经种栽下
但还没有开花
元军逼近,丞相陆秀夫
抱住王朝最后的皇帝赵昺
蹈海而亡
皇帝死时才八岁,如果他活着
该上小学二年级
他背着书包从树下走过
桂花已经开了
这是很小很小的花
就像他的年纪
抽烟的玛丽
我们说起了保罗
这个决绝的男人
三十年前离开了我们
准确地说,离开了玛丽
至今杳无音讯
三十年前的一个夜晚
他和妻子玛丽用完晚餐
开始一根根抽烟
他捻灭最后一个烟蒂
起身说:“亲爱的,我去街角买包烟!”
说罢,他推门走进了夜色
再也没有回来
玛丽从此也开始抽烟
一次次捻灭最后的烟蒂
老马
习惯了车把式、行人和汽车
也就习惯了不再奔跑
毛皮像一块黄昏
肮脏,松弛,已接近黑夜
金属的马蹄
使没有草的路更加漫长
我坐在县城嘈杂的小酒馆
看着你使尽力气低下头
把大车拉上了斜坡
却不懂用你的语言喊一声:
老马,进来喝一杯吧!
在圣玛丽娅医院
从白色的被单中,你向我伸出一只手
它修长,枯干,涂着蔻丹的指甲
像梅花,把冬天的树枝照耀
这些指甲,这些花,你一次次剪掉
又让它们一次次怒放
它们,位于你生活和身体的边缘
但总是这么洁净,这么鲜艳
哪怕在这所医院
抓住你的手,感到褐色的血管隆起
血液蠕动,从红色的指尖折返
记得你在书中说,在死亡的肉体中
指甲是最后腐烂的物质

姚风 诗人,翻译家,现为澳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获多个诗歌奖及葡萄牙总统颁授的“圣地亚哥宝剑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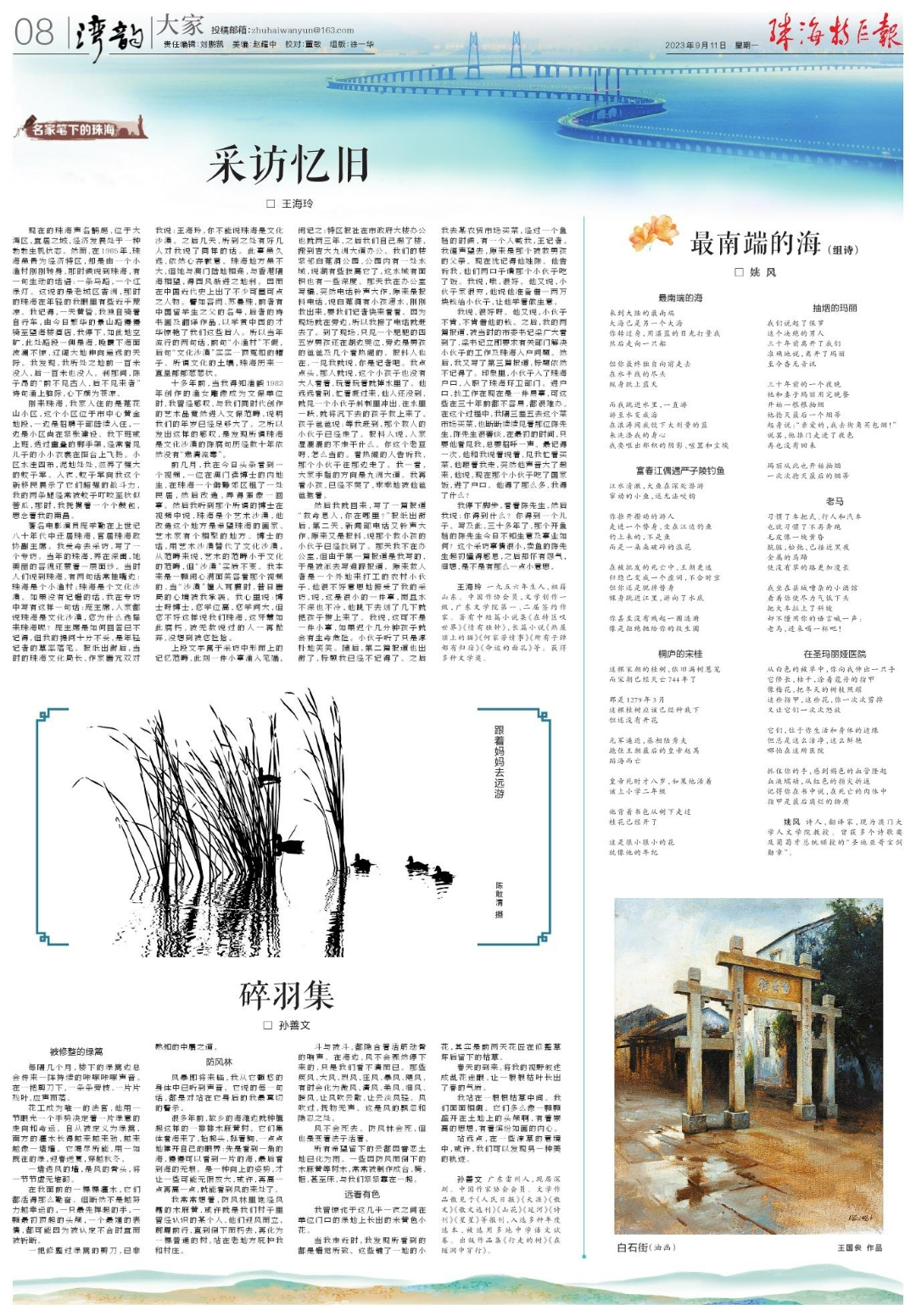
□王海玲

现在的珠海声名鹊起,位于大湾区,宜居之城,经济发展处于一种勃勃生机状态。然而,在1985年,珠海虽贵为经济特区,却是由一个小渔村刚刚转身,那时候说到珠海,有一句生动的话语:一条马路,一个红绿灯。这说的是老城区香洲,那时的珠海在年轻的我眼里有些近乎荒凉。我记得,一天黄昏,我独自骑着自行车,由今日繁华的景山路慢慢骑至望海楼酒店,我停下,如此地空旷,此处路段一侧是海,晚霞下海面波澜不惊,辽阔大地伸向遥远的天际。我发现,我所处之地前一百米没人,后一百米也没人。刹那间,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诗句涌上脑际,心下颇为苍凉。
刚来珠海,我家入住的是莲花山小区,这个小区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一边是招聘干部陆续入住,一边是小区尚在紧张建设。我下班或上班,透过重叠的脚手架,经常看见儿子的小小衣裳在阳台上飞扬。小区水洼四布,泥地处处,滋养了强大的蚊子军。入夜,蚊子军向我这个新移民展示了它们超强的战斗力,我的两条腿经常被蚊子叮咬至状似苦瓜,那时,我抚摸着一个个鼓包,思念着我的南昌。
著名电影演员庞学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迁居珠海,官居珠海政协副主席。我受命去采访,写了一个专访。当年的珠海,养在深闺,她美丽的容貌还蒙着一层面纱。当时人们说到珠海,有两句话常挂嘴边:珠海是个小渔村;珠海是个文化沙漠。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在专访中写有这样一句话:庞主席,人家都说珠海是文化沙漠,您为什么选择来珠海呢?庞主席是如何回答已不记得,但我的提问十分不妥,是年轻记者的草率落笔。报纸出街后,当时的珠海文化局长、作家唐亢双对我说:王海玲,你不能说珠海是文化沙漠。之后几天,所到之处有好几人对我说了同样的话。此事虽久远,依然心存歉意。珠海地方虽不大,但她与澳门陆地相连,与香港隔海相望,得西风渐进之地利。因而在中国近代史上出了不少可圈可点之人物。譬如容闳、苏曼殊,前者有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名号,后者的诗书画及翻译作品,以学贯中西的才华惊艳了我们这些后人。所以当年流行的两句话,前句“小渔村”不假,后句“文化沙漠”实实一顶冤扣的帽子。所谓文化的土壤,珠海历来一直呈郁郁葱葱状。
十多年前,当我得知潘鹤1982年创作的渔女雕像成为文保单位时,我曾经感叹,与我们同时代创作的艺术品竟然进入文保范畴,说明我们的年岁已经足够大了。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是发现所谓珠海是文化沙漠的陈腐句历经数十年依然没有“肃清流毒”。
前几月,我在今日头条看到一个视频,一位在澳门读博士的内地生,在珠海一个僻静郊区租了一处民居,然后改造,弄得蛮像一回事。然后我听到那个所谓的博士在视频中说,珠海是个艺术沙漠,他改造这个地方是希望珠海的画家、艺术家有个相聚的地方。博士的话,用艺术沙漠替代了文化沙漠,从范畴来说,艺术的范畴小于文化的范畴,但“沙漠”实质不变。我本来是一颗闲心满面笑容看那个视频的,当“沙漠”撞入耳膜时,昔日唐局的心境被我承袭。我心里说:博士呀博士,您学位高,您学问大,但您不好这样说我们珠海,这牙慧如此腐朽,被无数说过的人一再抛弃,没想到被您捡拾。
上段文字属于采访中形而上的记忆范畴,此刻一件小事涌入笔端,闲记之:特区报社在市政府大楼办公也就两三年,之后我们自己起了楼,搬到吉大九洲大道办公。我们的楼紧邻白莲洞公园,公园内有一处水域,说湖有些拔高它了,这水域有面积也有一些深度。那天我在办公室写稿,突然电话铃声大作,原来是报料电话,说白莲洞有小孩溺水,刚刚救出来,要我们记者快来看看。因为现场就在旁边,所以我接了电话就赶去了。到了现场,只见一个肥肥的四五岁男孩还在湖边哭泣,旁边是男孩的爸爸及几个看热闹的。报料人也在,一见我就说,你是记者吧。我点点头,那人就说,这个小孩子也没有大人看着,玩着玩着就掉水里了。他远远看到,忙着赶过来,他人还没到,就见一个小伙子斜刺里冲出,往水里一跃,就将沉下去的孩子救上来了。孩子爸爸说:等我赶到,那个救人的小伙子已经走了。报料人说,人家湿漉漉的不走干什么。你这个老豆呀,怎么当的。看热闹的人告诉我,那个小伙子往那边走了。我一看,大家手指的方向是九洲大道。我再看小孩,已经不哭了,乖乖地被他爸爸抱着。
然后我就回来,写了一篇报道“救命恩人,你在哪里?”报纸出街后,第二天,新闻部电话又铃声大作,原来又是报料,说那个救小孩的小伙子已经找到了。那天我不在办公室,但由于第一篇报道是我写的,于是被派去写追踪报道。原来救人者是一个外地来打工的农村小伙子,他很不好意思地接受了我的采访,说,这是很小的一件事,而且水不深也不冷,他跳下去划了几下就把孩子捞上来了。我说,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如果迟个几分钟孩子就会有生命危险。小伙子听了只是淳朴地笑笑。随后,第二篇报道也出街了,标题我已经不记得了。之后我去某农贸市场买菜,经过一个鱼档的时候,有一个人喊我,王记者。我循声望去,原来是那个被救男孩的父亲。现在犹记得他姓陈。他告诉我,他们两口子请那个小伙子吃了饭。我说,哦,很好。他又说,小伙子家很穷,他说他准备借一两万块钱给小伙子,让他学着做生意。
我说,很好呀。他又说,小伙子不肯,不肯借他的钱。之后,我的两篇报道,被当时的市委书记梁广大看到了,梁书记立即要求有关部门解决小伙子的工作及珠海入户问题。然后,我又写了第三篇报道,标题依然不记得了。印象里,小伙子入了珠海户口,入职了珠海环卫部门。进户口、找工作在现在是一件易事,可这些在三十年前都不容易,都很难办。在这个过程中,我隔三差五去这个菜市场买菜,也断断续续见着那位陈先生,陈先生很善谈,在最初的时间,只要他看见我,总要招呼一声。最记得一次,他和我说着说着,见我忙着买菜,他跟着我走,突然他声音大了起来,他说,现在那个小伙子吃了国家饭,进了户口。他得了那么多,我得了什么?
我停下脚步,看着陈先生,然后我说:你得到什么?你得到一个儿子。写及此,三十多年了,那个开鱼档的陈先生今日不知生意及事业如何?这个采访事情很小,卖鱼的陈先生起初懂得感恩,之后却怀有怨气,细想,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小意思。

王海玲 一九五六年生人,祖籍山东。中国作协会员,文学创作一级,广东文学院第一、二届签约作家。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在特区叹世界》《情有独钟》,长篇小说《热屋顶上的猫》《何家芳情事》《所有子弹都有归宿》《命运的面孔》等。获得多种文学奖。


跟着妈妈去远游。陈敢清 摄


□孙善文
被修整的绿篱
每隔几个月,楼下的绿篱边总会传来一阵持续的咔嚓咔嚓声音。在一把剪刀下,一条条旁枝、一片片残叶,应声而落。
花工成为唯一的法官,他用一节眼光一个手势决定着一片绿意的走向和命运。自从被定义为绿篱,南方的灌木长得越来越来劲,越来越像一堵墙。它竭尽所能,用一如既往的绿,迎春送夏,穿越秋冬。
一堵透风的墙,是风的骨头,将一节节虚无堆砌。
在我面前的一棵棵灌木,它们都活得那么勤奋。但断然不是越努力越幸运的,一只最先挥起的手,一颗最初顶起的头颅,一个最媚的表情,都可能因为被认定不合时宜而被斩断。
一把修整过绿篱的剪刀,已非熟知的中庸之道。
防风林
风暴即将来临,我从它颤悠的身体中已听到声音。它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站在它身后的我最真切的警示。
很多年前,故乡的海滩边就种植起这样的一排排木麻黄树。它们集体看海来了,抬起头,挺着胸,一点点地撑开自己的眼界:先是看到一角的海,慢慢可以看到一片的海,最后看到海的无垠。是一种向上的姿势,才让一些可能无限放大,或许,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就能看到风的来处了。
我常常想着,防风林里饱经风霜的木麻黄,或许就是我们村子里曾经认识的某个人,他们迎风而立,踯躅前行,直到倒下而朽去,再化为一棵普通的树,站在老地方庇护我和村庄。
斗与被斗,都隐含着活筋动骨的响声。在海边,风不会骤然停下来的,只是我们看不清而已。那些疾风、大风、烈风、狂风、暴风、飓风,有时会化为微风、清风、柔风、细风、暖风,让风吹云散,让云淡风轻。风吹过,抚物无声。这是风的飘忽和隐忍之处。
风不会死去。防风林会死,但也是变着法子活着。
所有希望留下的云都因眷恋土地已化为雨。一些因防风而倒下的木麻黄等树木,常常被制作成台、椅、柜,甚至床,与我们紧紧靠在一起。
远看有色
我曾惊诧于这几乎一夜之间在单位门口的绿地上长出的米黄色小花。
当我走近时,我发现所看到的都是错觉所致。这些铺了一地的小花,其实是前两天花匠在修整草坪后留下的枯草。
春天的到来,将我的视野叙述成乱花迷眼,让一根根枯叶长出了春的气质。
我站在一根根枯草中间。我们面面相觑。它们多么像一颗颗盛开在土地上的头颅啊,有着崇高的思想,有着缤纷如画的内心。
站远点,在一些潦草的意境中,或许,我们可以发现另一种美的轨迹。

孙善文 广东雷州人,现居深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天涯》《散文》《散文选刊》《山花》《延河》《诗刊》《星星》等报刊,入选多种年度选本,被选用多地中学语文试卷。出版作品集《行走的树》《在隧洞中穿行》。

白石街(油画)。王国俊 作品


□姚风

最南端的海
来到大陆的最南端
大海已是另一个大海
你转过身,用湛蓝的目光打量我
然后走向一只船
但你最终独自向前走去
在水平线的尽头
纵身跃上蓝天
而我跳进水里,一直游
游至水变成海
在浪涛间我饮下大剂量的蓝
来洗涤我的身心
我要呕出郁积的阴影、喧嚣和尘埃
富春江偶遇严子陵钓鱼
江水清澈,大鱼在深处潜游
窜动的小鱼,还无法咬钩
你推开攒动的游人
走进一个替身,坐在江边钓鱼
钓上来的,不是鱼
而是一朵朵破碎的浪花
在被批发的死亡中,王朝更迭
归隐已变成一个虚词,不合时宜
但你还是脱掉替身
裸身跳进江里,游向了水底
你甚至没有溅起一圈涟漪
像是拒绝抛给你的救生圈
桐庐的宋桂
这棵宋朝的桂树,依旧满树葱茏
而宋朝已经灭亡744年了
那是1279年3月
这棵桂树应该已经种栽下
但还没有开花
元军逼近,丞相陆秀夫
抱住王朝最后的皇帝赵昺
蹈海而亡
皇帝死时才八岁,如果他活着
该上小学二年级
他背着书包从树下走过
桂花已经开了
这是很小很小的花
就像他的年纪
抽烟的玛丽
我们说起了保罗
这个决绝的男人
三十年前离开了我们
准确地说,离开了玛丽
至今杳无音讯
三十年前的一个夜晚
他和妻子玛丽用完晚餐
开始一根根抽烟
他捻灭最后一个烟蒂
起身说:“亲爱的,我去街角买包烟!”
说罢,他推门走进了夜色
再也没有回来
玛丽从此也开始抽烟
一次次捻灭最后的烟蒂
老马
习惯了车把式、行人和汽车
也就习惯了不再奔跑
毛皮像一块黄昏
肮脏,松弛,已接近黑夜
金属的马蹄
使没有草的路更加漫长
我坐在县城嘈杂的小酒馆
看着你使尽力气低下头
把大车拉上了斜坡
却不懂用你的语言喊一声:
老马,进来喝一杯吧!
在圣玛丽娅医院
从白色的被单中,你向我伸出一只手
它修长,枯干,涂着蔻丹的指甲
像梅花,把冬天的树枝照耀
这些指甲,这些花,你一次次剪掉
又让它们一次次怒放
它们,位于你生活和身体的边缘
但总是这么洁净,这么鲜艳
哪怕在这所医院
抓住你的手,感到褐色的血管隆起
血液蠕动,从红色的指尖折返
记得你在书中说,在死亡的肉体中
指甲是最后腐烂的物质

姚风 诗人,翻译家,现为澳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获多个诗歌奖及葡萄牙总统颁授的“圣地亚哥宝剑勋章”。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