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苗秀侠
高德地图告诉我,我的故乡苗老集,和亳州城之间的距离是63公里,开车需要一个小时。这条贯穿南北的高速路,拉近了我和亳州——这个文脉丰沛、带给我传奇和遐想的城市的距离。时光倏忽,尽管早已完成一次次的拜谒,但若干年来,只要一想到这座城池,就会文思泉涌,就会浮想联翩,情不能抑,就会忍不住跑过去,跟她照个面。
少年的忧伤
最初知道亳州,是从母亲唱的戏文里获得的。那时候亳州叫亳县。
学龄前,趴在小板凳上捏泥碗碗,听妈妈小声唱河南豫剧,其中几句听得我耳熟能详:“花木兰羞答答施礼拜上,尊一声贺元帅细听端详,阵前的花木棣就是末将,我原名叫花木兰是个女郎……”
花木兰是谁?见母亲唱得情真意切,眉眼里都是对花木兰的喜爱,忍不住问道。
花木兰离得不远哪,就在北边那一片。母亲讲述着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然后,手朝北一指,喏,花木兰的家,就是亳县那个地方。
原来,那个叫花木兰又叫花木棣、武功高强女扮男装的武林高手,就是北边不远的亳县人哪!便对亳县有了遐想。小孩子的遐想抻不远,简单,在脑子里过一过,又站在村子北边的一只石磙上,北望一番,仿佛看到穿战袍握银枪的女子,骑着高头大马,顺着麦地垄跃马扬鞭而来,甚至带来一阵呐喊声。这经验来自于乡村舞台,民间剧团演唱的武戏,演员们的穿着打扮、一招一式,就是这种样子。那么,带兵打仗的花木兰,也一定是这种样子喽。
后来的戏文里,让我知道了白脸奸臣曹操、会治百病的名医华佗,都是亳县人。对亳县的神往,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而她却远在天边之外。因此,北望亳县成了我少时唯一的忧伤。这种忧伤止于十四岁。
第一次私游
十四岁的暑假,与同学相约,去远点的地方玩玩,就去了玄集看茨河闸。对着滔滔茨河水唱歌跳舞,又沿着河堤的杨树林子疯跑尖叫,欢乐一整天。仍觉不过瘾。我们可以去亳县!我的提议让同学兴奋,立刻点头同意。在学校,我们两个最铁,一起跟男生打架,一起写小说,一起散步谈理想,还各自取了笔名。那时候,《清明》《小说月报》已经有了,我们成绩好,可以很自信地朝老师借杂志看。就这样,我和同学成功策划了亳县之旅。之所以敢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玩,个中底气,是同学的表叔就在亳县工作。
说起来很低智,但仍把各自的父母骗住了。我跟父母说去同学家玩三天,同学的版本跟我如出一辙。两个少女就这样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私游。那时候没电话,没微信,相隔七八里路的村庄,可以玩三十六计里的瞒天过海。
一大早出发,先从苗老集坐汽车,朝西走七十华里,再在三角园转车去亳县。到亳县县城时,天快黑透了。一直难忘在陌生县城汽车站猛丁出站的感觉,浓厚的陌生感,仿佛一张黑毯,呼啦将人裹严。一路说笑此刻息声,不敢兴奋,两个小孩努力装出胆大妄为的样子,却腿肚子暗自打颤,最终,乖乖地快速钻进站东小旅馆。那时候不流行研学活动,旅馆老板娘见到两个背黄书包的小姑娘,端出应有的担心,她慈眉善目,问道:同学是走亲戚吗?立刻点头,眼泪几乎就要掉出来。晚饭也不敢出来吃,就那样团在床上,紧张到天亮。
天亮的好处是肥人胆。亳县县城处处阳光,树叶清亮,市声悠扬。两人饱餐一顿嘛糊油炸馍,立马来了精神,为昨晚的萎顿胆小羞愧不已。既来之则安之,一定完成亳县的首游。亳县既然做过都城,一定有与众不同之处。果然,老石板街漂亮至极,厚实光亮的石板,平生第一次见,两人蹲下身,用手摸石板,尽管是暑天,仍觉石板透着沁心凉意。
还有街两边的老房子,虽非高楼大厦(那个年代高楼不多),却古色古香,有着不怒自威的风姿。那时候年少,尚不懂这种风姿就是帝都的文化气场。当然,除了老房子,亳县的其他街道和别的县城没多大区别。一边在街上走,一边东张西望,问了许多人,终于找到同学表叔工作的大院,却不料,表叔升了职,到某镇当站长去了。因为找不着表叔,没有依靠,胆子再次变小,一番商量后,两人决定就此结束亳县之旅。
背着黄书包,买了两只烧饼,急忙赶往汽车站,坐上回程车,辗转到苗老集时,鸡都上笼了。先一同去同学家住一晚,第二天再一起去我家。总算,既私游了亳县,又圆了谎言。
现在想来,亳州的首游,尽管没有见到和花木兰有关的影儿,却成就了一篇像模像样的小说。题材是从黑白电影里高仿来的:送鸡毛信,接头暗号,游击队长留着大胡子(同学所说的表叔模样)。送信途中,惊险连连,遇见鬼子的巡逻队,在小旅馆避险……那篇小说有一万字,真是可读,先是在班里被同学传看,又被隔壁班同学借去养眼。首游亳县成就了我与此城的传奇,也开启了我的写作之旅。
花木兰的花海
此次来亳州,是看芍药花海的。去花海的路上,见道路标牌写着“木兰路”,沟渠叫作“木兰沟”,可见,花木兰的元素无处不在。木兰沟和花木兰有关系吗?山东蓬莱有个村庄叫木兰沟,为嘛这个沟也叫木兰沟?陪同赏花的当地村干部马上当起了解说员,很快给我补了一课:这条木兰沟,在上世纪的1958年开挖,是众多未出阁的姑娘,用两个月时间圆满完成的水利大工程,她们拼搏上阵,挥洒香汗,发扬的就是花木兰不怕吃苦、勇往直前的精神。沟渠挖好后,就取名叫木兰沟。
在走近花海的一瞬,我毫不犹豫地把四季花海,命名为“花木兰的花海”。想必木兰姐姐也是这么想的。她不仅羞答答地承认自己女扮男装替父从军,金戈铁马,还能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换下战时袍,着上女儿装,可见也是个爱美的女子。面对万亩大花海,木兰姐姐一定于低眉浅笑之间,顺手拈来一朵芍花,别在发髻之上,对镜顾盼生辉呢。
在花木兰的花海里穿行,满身花香。亳州的好,亳州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让任何到过亳州的人,都情不能抑,这就是文脉的力量。
亳州的文脉,必将接济每一个爱她的人。
苗秀侠 中国作协会员,文学创作一级。在《小说选刊》《中国作家》《北京文学》《芳草》《作品》《长江文艺》等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遍地庄稼》《迷惘的庄稼》及长篇小说《农民的眼睛》《皖北大地》《大浍水》等。曾获老舍散文奖、安徽省政府社科奖、北京文学奖、安徽省“五个一工程”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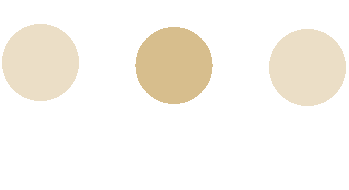

海上风景(油画) 金凡 作品
——张恨水先生的《平沪通车》
□伍立杨
《平沪通车》,张恨水先生的名作。时代背景乃1935年前后。
银行家胡子云携带巨款,乘坐火车由北平赴上海,他具有一副政客的体貌(白晰乌须而态度稳重),正做着醇酒妇人的春梦。他在餐车邂逅没有买到卧铺票的绝色女郎柳絮春,乃聊之,竟然有远房亲戚的瓜葛。他见色起念,百计接近,不知女郎早有预谋,多番转折后,从他日思夜梦的虚拟幻境进入实体操作,当夜便坐一处,度过火车上的浪漫春宵。次日旧情重温,晚上到达苏州站时,停车较长时间,当银行家醒来,火车已将抵上海,他的巨款早已不翼而飞——游戏已经结束。颠鸾倒凤辉煌胜利之后,立刻就暴露了它的本质——骗术。银行家傻了,随后他疯了。又过了几年,穷愁潦倒的他又在苏州站遇一女流,像极柳絮春,他触景生情,追了上去……
火车车轮滚滚,而情节也随之吊诡谲奇。这么一个柔性、艳情的故事,写得惊险百出,笔力不稍衰。其叙事风格是稳重大方而波澜迭起。
主人公闲情横流,放肆尘想。对其艳遇益发坚信不疑。女角对其控制,也如机床齿轮之咬合,严丝合缝,动弹不得;最能迷惑人的九尾狐狸精,或如运用阿斗,心算之间就钦定了他的天下。
江山可改,人性难移,在一个混乱冥顽的物质社会,若有西施王嫱倩影入梦,那多不是巧笑美目的欢好,而是白骨精取命剜心的利刃。胡先生一时糊涂,为一己的欲望所牵制,而击毁在对方人性贪欲的遏制之下。
恨水先生的叙述笔法,有这样一种魔力,丝丝入扣,绵密紧凑,而又一波三折;每每有那关键之点,端的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拆白党的女角,似乎也丝毫没有佻达不雅的作态,女角的诱惑过程,她的破绽好像微风掀起的衣襟,亦藏亦隐,很快又是夜阑风静毂纹平,也即说,您发现了破绽、不对劲,但您却甘愿受骗——您发现了骗局却并不相信这是一个骗局,您把吴钩看了,把栏杆拍遍,也还是无人会登临意。他老先生这一支健笔,好像万吨闸门,肩住了宏深的水泊,不动声色,到了开闸的时候,只见万钧雷霆,咆哮而出,悲剧之不可挽回,由是定型。当中包含的洞察与解构,稳稳当当的立定在那里。写到女郎苏州下车一段,直是惊心动魄,好像身历一场大变故一样,种种处心积虑的计谋重锤一样砸着人心。
胡子云最后疯狂了。他又来到火车站,又看到了和先前的他一样身份装束的大亨男子,正在及时地为那不相识的妙龄女郎大献殷勤。子云叫道,喂!你不怕上当吗?“然而天下上女人当的,只管上当,追求女人的,还在尽力地追求……”读者似不能因有惨痛之一面,而忽略其有教育针砭意义之一面。西方有句谚语,说:你骗我第一次,你应该感到羞愧;你骗我第二次,我应该感到羞愧。但对于一种深入骨髓的骗术,要后悔却噬脐莫及。
女人善敲竹杠者,西方谓之挖金姑娘。至不惜以最欺诈之手段达至其目标,谋划之深沉、手腕之灵敏,恰与奸商为富不仁上下其手配为佳偶。风姿绰约,明目善睐,外在身段无限柔软,而内里同样硬狠心肠。是蛇蝎,谁近之,则咬谁。此类人在社会交际中,所伤害者,为不同的个体,所愚弄颠倒者乃是无数人间良善、无数的无告小民。巨奸大恶,和拆白党女角实在同一城府,同一手腕,同一邪恶;只是前者玩弄生命,杀人无算,而美其名曰理想社会,幸存者之抚膺痛哭,并不能消泯其伤害于万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我还在读高中,初读此书,为其哀感顽艳所眩惑,久之难以释怀。
“呜的一声,火车开了,把这个疯魔了的汉子扔在苏州站上,大雪飞舞着,寒风呼呼的空气里,他还在叫着呢!”
伍立杨 198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其后长期任人民日报社记者、主任编辑。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中国1911》《民国幕僚史话》《潜龙在渊-章太炎传》《铁血黄花》等三十余部。曾任海南省第四届作家协会副主席、海南省第五届政协委员、海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四川省作家协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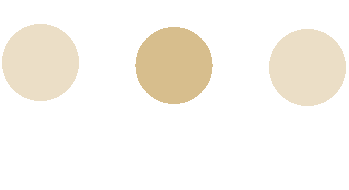
□韩少君
向我敞开的样子
湿润的山峦,迎面而来
没有人能借助它的力量
云层之下,本质上没有
什么变化,全都是向我
敞开的样子。木棉逢春粤北,石巷重获生机
R.S.托马斯隔海啸叫:
“新绿将用她的烈焰把你洗净”
难怪,几只洗净的短尾鸟,吵闹着
从更远的山涧,一直跳到了溪口。
迁徙
一切都是那么好
恰到好处的好,确如
某人所言,活着
就像假设的一样
一切都是那么好
你提着一小吊冻肉
走街串巷,身体
陷于阴霾,在街角
光滑的墙面上,你
突然发现自己,真是
奇怪,你开始有了列宁的
发线,你鼓动一下自己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这次,你要模仿他的标准姿势
旁若无人,大街上
也好像没有人类,只有
一条小狗跟着,你
提着一小吊冻肉,只有
它明白这是在迁徙,所以
它跟得很紧,跑前,跑后
轶事
星星北去
头向后仰
阅读出现裂缝
的时候,狂风
趁机吹进丛林
摇动海滨硕果
也掀开他
“灰烬色头发”。
穿过昏暗街区
老头泪光充盈
又一次在那棵
阔叶树下张望。
忆与基诺族兄弟共饮
短暂与柔弱
需要一杯酒来
取消,春日
在小国边境
大醉之后
走进密林
与巨兽对视。
我的基诺族兄弟
在我脸上
涂抹吉祥的黑炭。
山谷在合拢
星辰,杜鹃
腐叶呀幼蛇
几只云雀还
在头顶欢叫。
虎爪山秋吟
深秋,虎爪山是危险的
二十年过去了,险象依然
一棵红桦站在林木中间,是危险的
众人走过去,她们好像都没有苏醒
我也是麻醉之人,虎爪山上
一粒阳光,让我顿时清醒
众人靠紧一簇车矢菊,说好了
一起跳,他们乐于,在此空跳。
韩少君 男,1964年出生,中国作协会员,湖北省作协委员,湖北荆门市文联副主席,荆门市作协书记、副主席;著有诗集《倾听》《你喜欢的沙文主义》《洗浴过的工作阶级》《夜里会有什么声音》等六部;获“长江文艺”诗歌奖、“或者”诗歌奖、“朝阳”文学奖等;曾主编中国唯美诗歌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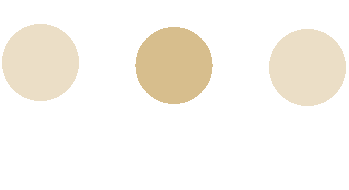
□罗春柏
1
沙滩洁白的肌肤
细腻柔软
那尊礁石
却失去圆润
嶙峋的瘦骨
在涛声中颤栗
我不禁发问
如果我一直站在这里
大海将怎样为我造型
2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涌动的激情
是体内不灭的火吗
扑面而来,想把
尘世淘洗干净
可是,谁能理解呢
我穿一袭礼服
迎候你,细听浪涛诵读
一波一波心经
3
一挂风帆
飘近又飘远
仿佛在丈量着
一色的水天
我不过问世事
只想直面一片汪洋
把尘心交出
在烟波中滋养
4
夕阳有情
把我的身影
投入泱泱的水里
我不希望成为
骤起骤落的浪花
却在想着
我能否成为
一个分子
融入大海这个家庭
共渡
走出尘嚣的门
蹚过一水之湄
我在阳光下
牵来一道彩虹
在夜里点燃渔火
照亮世间的昏暗
我不是岸上的花
不断绽放不断凋落
我没有流连湖泊和远山
只飘动在无边的湛蓝
我邀海鸥共舞
还在最低处
陪伴风帆远渡
罗春柏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歌作品见于国内多种名刊。有作品入选中国年度诗歌多种选本。诗集《枝头的绿羽》获广东省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苗秀侠
高德地图告诉我,我的故乡苗老集,和亳州城之间的距离是63公里,开车需要一个小时。这条贯穿南北的高速路,拉近了我和亳州——这个文脉丰沛、带给我传奇和遐想的城市的距离。时光倏忽,尽管早已完成一次次的拜谒,但若干年来,只要一想到这座城池,就会文思泉涌,就会浮想联翩,情不能抑,就会忍不住跑过去,跟她照个面。
少年的忧伤
最初知道亳州,是从母亲唱的戏文里获得的。那时候亳州叫亳县。
学龄前,趴在小板凳上捏泥碗碗,听妈妈小声唱河南豫剧,其中几句听得我耳熟能详:“花木兰羞答答施礼拜上,尊一声贺元帅细听端详,阵前的花木棣就是末将,我原名叫花木兰是个女郎……”
花木兰是谁?见母亲唱得情真意切,眉眼里都是对花木兰的喜爱,忍不住问道。
花木兰离得不远哪,就在北边那一片。母亲讲述着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然后,手朝北一指,喏,花木兰的家,就是亳县那个地方。
原来,那个叫花木兰又叫花木棣、武功高强女扮男装的武林高手,就是北边不远的亳县人哪!便对亳县有了遐想。小孩子的遐想抻不远,简单,在脑子里过一过,又站在村子北边的一只石磙上,北望一番,仿佛看到穿战袍握银枪的女子,骑着高头大马,顺着麦地垄跃马扬鞭而来,甚至带来一阵呐喊声。这经验来自于乡村舞台,民间剧团演唱的武戏,演员们的穿着打扮、一招一式,就是这种样子。那么,带兵打仗的花木兰,也一定是这种样子喽。
后来的戏文里,让我知道了白脸奸臣曹操、会治百病的名医华佗,都是亳县人。对亳县的神往,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而她却远在天边之外。因此,北望亳县成了我少时唯一的忧伤。这种忧伤止于十四岁。
第一次私游
十四岁的暑假,与同学相约,去远点的地方玩玩,就去了玄集看茨河闸。对着滔滔茨河水唱歌跳舞,又沿着河堤的杨树林子疯跑尖叫,欢乐一整天。仍觉不过瘾。我们可以去亳县!我的提议让同学兴奋,立刻点头同意。在学校,我们两个最铁,一起跟男生打架,一起写小说,一起散步谈理想,还各自取了笔名。那时候,《清明》《小说月报》已经有了,我们成绩好,可以很自信地朝老师借杂志看。就这样,我和同学成功策划了亳县之旅。之所以敢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玩,个中底气,是同学的表叔就在亳县工作。
说起来很低智,但仍把各自的父母骗住了。我跟父母说去同学家玩三天,同学的版本跟我如出一辙。两个少女就这样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私游。那时候没电话,没微信,相隔七八里路的村庄,可以玩三十六计里的瞒天过海。
一大早出发,先从苗老集坐汽车,朝西走七十华里,再在三角园转车去亳县。到亳县县城时,天快黑透了。一直难忘在陌生县城汽车站猛丁出站的感觉,浓厚的陌生感,仿佛一张黑毯,呼啦将人裹严。一路说笑此刻息声,不敢兴奋,两个小孩努力装出胆大妄为的样子,却腿肚子暗自打颤,最终,乖乖地快速钻进站东小旅馆。那时候不流行研学活动,旅馆老板娘见到两个背黄书包的小姑娘,端出应有的担心,她慈眉善目,问道:同学是走亲戚吗?立刻点头,眼泪几乎就要掉出来。晚饭也不敢出来吃,就那样团在床上,紧张到天亮。
天亮的好处是肥人胆。亳县县城处处阳光,树叶清亮,市声悠扬。两人饱餐一顿嘛糊油炸馍,立马来了精神,为昨晚的萎顿胆小羞愧不已。既来之则安之,一定完成亳县的首游。亳县既然做过都城,一定有与众不同之处。果然,老石板街漂亮至极,厚实光亮的石板,平生第一次见,两人蹲下身,用手摸石板,尽管是暑天,仍觉石板透着沁心凉意。
还有街两边的老房子,虽非高楼大厦(那个年代高楼不多),却古色古香,有着不怒自威的风姿。那时候年少,尚不懂这种风姿就是帝都的文化气场。当然,除了老房子,亳县的其他街道和别的县城没多大区别。一边在街上走,一边东张西望,问了许多人,终于找到同学表叔工作的大院,却不料,表叔升了职,到某镇当站长去了。因为找不着表叔,没有依靠,胆子再次变小,一番商量后,两人决定就此结束亳县之旅。
背着黄书包,买了两只烧饼,急忙赶往汽车站,坐上回程车,辗转到苗老集时,鸡都上笼了。先一同去同学家住一晚,第二天再一起去我家。总算,既私游了亳县,又圆了谎言。
现在想来,亳州的首游,尽管没有见到和花木兰有关的影儿,却成就了一篇像模像样的小说。题材是从黑白电影里高仿来的:送鸡毛信,接头暗号,游击队长留着大胡子(同学所说的表叔模样)。送信途中,惊险连连,遇见鬼子的巡逻队,在小旅馆避险……那篇小说有一万字,真是可读,先是在班里被同学传看,又被隔壁班同学借去养眼。首游亳县成就了我与此城的传奇,也开启了我的写作之旅。
花木兰的花海
此次来亳州,是看芍药花海的。去花海的路上,见道路标牌写着“木兰路”,沟渠叫作“木兰沟”,可见,花木兰的元素无处不在。木兰沟和花木兰有关系吗?山东蓬莱有个村庄叫木兰沟,为嘛这个沟也叫木兰沟?陪同赏花的当地村干部马上当起了解说员,很快给我补了一课:这条木兰沟,在上世纪的1958年开挖,是众多未出阁的姑娘,用两个月时间圆满完成的水利大工程,她们拼搏上阵,挥洒香汗,发扬的就是花木兰不怕吃苦、勇往直前的精神。沟渠挖好后,就取名叫木兰沟。
在走近花海的一瞬,我毫不犹豫地把四季花海,命名为“花木兰的花海”。想必木兰姐姐也是这么想的。她不仅羞答答地承认自己女扮男装替父从军,金戈铁马,还能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换下战时袍,着上女儿装,可见也是个爱美的女子。面对万亩大花海,木兰姐姐一定于低眉浅笑之间,顺手拈来一朵芍花,别在发髻之上,对镜顾盼生辉呢。
在花木兰的花海里穿行,满身花香。亳州的好,亳州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让任何到过亳州的人,都情不能抑,这就是文脉的力量。
亳州的文脉,必将接济每一个爱她的人。
苗秀侠 中国作协会员,文学创作一级。在《小说选刊》《中国作家》《北京文学》《芳草》《作品》《长江文艺》等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遍地庄稼》《迷惘的庄稼》及长篇小说《农民的眼睛》《皖北大地》《大浍水》等。曾获老舍散文奖、安徽省政府社科奖、北京文学奖、安徽省“五个一工程”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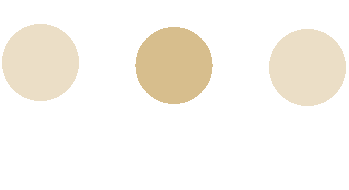

海上风景(油画) 金凡 作品
——张恨水先生的《平沪通车》
□伍立杨
《平沪通车》,张恨水先生的名作。时代背景乃1935年前后。
银行家胡子云携带巨款,乘坐火车由北平赴上海,他具有一副政客的体貌(白晰乌须而态度稳重),正做着醇酒妇人的春梦。他在餐车邂逅没有买到卧铺票的绝色女郎柳絮春,乃聊之,竟然有远房亲戚的瓜葛。他见色起念,百计接近,不知女郎早有预谋,多番转折后,从他日思夜梦的虚拟幻境进入实体操作,当夜便坐一处,度过火车上的浪漫春宵。次日旧情重温,晚上到达苏州站时,停车较长时间,当银行家醒来,火车已将抵上海,他的巨款早已不翼而飞——游戏已经结束。颠鸾倒凤辉煌胜利之后,立刻就暴露了它的本质——骗术。银行家傻了,随后他疯了。又过了几年,穷愁潦倒的他又在苏州站遇一女流,像极柳絮春,他触景生情,追了上去……
火车车轮滚滚,而情节也随之吊诡谲奇。这么一个柔性、艳情的故事,写得惊险百出,笔力不稍衰。其叙事风格是稳重大方而波澜迭起。
主人公闲情横流,放肆尘想。对其艳遇益发坚信不疑。女角对其控制,也如机床齿轮之咬合,严丝合缝,动弹不得;最能迷惑人的九尾狐狸精,或如运用阿斗,心算之间就钦定了他的天下。
江山可改,人性难移,在一个混乱冥顽的物质社会,若有西施王嫱倩影入梦,那多不是巧笑美目的欢好,而是白骨精取命剜心的利刃。胡先生一时糊涂,为一己的欲望所牵制,而击毁在对方人性贪欲的遏制之下。
恨水先生的叙述笔法,有这样一种魔力,丝丝入扣,绵密紧凑,而又一波三折;每每有那关键之点,端的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拆白党的女角,似乎也丝毫没有佻达不雅的作态,女角的诱惑过程,她的破绽好像微风掀起的衣襟,亦藏亦隐,很快又是夜阑风静毂纹平,也即说,您发现了破绽、不对劲,但您却甘愿受骗——您发现了骗局却并不相信这是一个骗局,您把吴钩看了,把栏杆拍遍,也还是无人会登临意。他老先生这一支健笔,好像万吨闸门,肩住了宏深的水泊,不动声色,到了开闸的时候,只见万钧雷霆,咆哮而出,悲剧之不可挽回,由是定型。当中包含的洞察与解构,稳稳当当的立定在那里。写到女郎苏州下车一段,直是惊心动魄,好像身历一场大变故一样,种种处心积虑的计谋重锤一样砸着人心。
胡子云最后疯狂了。他又来到火车站,又看到了和先前的他一样身份装束的大亨男子,正在及时地为那不相识的妙龄女郎大献殷勤。子云叫道,喂!你不怕上当吗?“然而天下上女人当的,只管上当,追求女人的,还在尽力地追求……”读者似不能因有惨痛之一面,而忽略其有教育针砭意义之一面。西方有句谚语,说:你骗我第一次,你应该感到羞愧;你骗我第二次,我应该感到羞愧。但对于一种深入骨髓的骗术,要后悔却噬脐莫及。
女人善敲竹杠者,西方谓之挖金姑娘。至不惜以最欺诈之手段达至其目标,谋划之深沉、手腕之灵敏,恰与奸商为富不仁上下其手配为佳偶。风姿绰约,明目善睐,外在身段无限柔软,而内里同样硬狠心肠。是蛇蝎,谁近之,则咬谁。此类人在社会交际中,所伤害者,为不同的个体,所愚弄颠倒者乃是无数人间良善、无数的无告小民。巨奸大恶,和拆白党女角实在同一城府,同一手腕,同一邪恶;只是前者玩弄生命,杀人无算,而美其名曰理想社会,幸存者之抚膺痛哭,并不能消泯其伤害于万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我还在读高中,初读此书,为其哀感顽艳所眩惑,久之难以释怀。
“呜的一声,火车开了,把这个疯魔了的汉子扔在苏州站上,大雪飞舞着,寒风呼呼的空气里,他还在叫着呢!”
伍立杨 198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其后长期任人民日报社记者、主任编辑。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中国1911》《民国幕僚史话》《潜龙在渊-章太炎传》《铁血黄花》等三十余部。曾任海南省第四届作家协会副主席、海南省第五届政协委员、海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四川省作家协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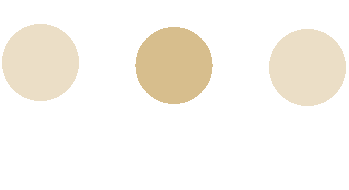
□韩少君
向我敞开的样子
湿润的山峦,迎面而来
没有人能借助它的力量
云层之下,本质上没有
什么变化,全都是向我
敞开的样子。木棉逢春粤北,石巷重获生机
R.S.托马斯隔海啸叫:
“新绿将用她的烈焰把你洗净”
难怪,几只洗净的短尾鸟,吵闹着
从更远的山涧,一直跳到了溪口。
迁徙
一切都是那么好
恰到好处的好,确如
某人所言,活着
就像假设的一样
一切都是那么好
你提着一小吊冻肉
走街串巷,身体
陷于阴霾,在街角
光滑的墙面上,你
突然发现自己,真是
奇怪,你开始有了列宁的
发线,你鼓动一下自己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这次,你要模仿他的标准姿势
旁若无人,大街上
也好像没有人类,只有
一条小狗跟着,你
提着一小吊冻肉,只有
它明白这是在迁徙,所以
它跟得很紧,跑前,跑后
轶事
星星北去
头向后仰
阅读出现裂缝
的时候,狂风
趁机吹进丛林
摇动海滨硕果
也掀开他
“灰烬色头发”。
穿过昏暗街区
老头泪光充盈
又一次在那棵
阔叶树下张望。
忆与基诺族兄弟共饮
短暂与柔弱
需要一杯酒来
取消,春日
在小国边境
大醉之后
走进密林
与巨兽对视。
我的基诺族兄弟
在我脸上
涂抹吉祥的黑炭。
山谷在合拢
星辰,杜鹃
腐叶呀幼蛇
几只云雀还
在头顶欢叫。
虎爪山秋吟
深秋,虎爪山是危险的
二十年过去了,险象依然
一棵红桦站在林木中间,是危险的
众人走过去,她们好像都没有苏醒
我也是麻醉之人,虎爪山上
一粒阳光,让我顿时清醒
众人靠紧一簇车矢菊,说好了
一起跳,他们乐于,在此空跳。
韩少君 男,1964年出生,中国作协会员,湖北省作协委员,湖北荆门市文联副主席,荆门市作协书记、副主席;著有诗集《倾听》《你喜欢的沙文主义》《洗浴过的工作阶级》《夜里会有什么声音》等六部;获“长江文艺”诗歌奖、“或者”诗歌奖、“朝阳”文学奖等;曾主编中国唯美诗歌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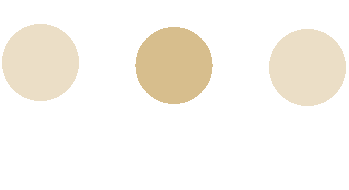
□罗春柏
1
沙滩洁白的肌肤
细腻柔软
那尊礁石
却失去圆润
嶙峋的瘦骨
在涛声中颤栗
我不禁发问
如果我一直站在这里
大海将怎样为我造型
2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涌动的激情
是体内不灭的火吗
扑面而来,想把
尘世淘洗干净
可是,谁能理解呢
我穿一袭礼服
迎候你,细听浪涛诵读
一波一波心经
3
一挂风帆
飘近又飘远
仿佛在丈量着
一色的水天
我不过问世事
只想直面一片汪洋
把尘心交出
在烟波中滋养
4
夕阳有情
把我的身影
投入泱泱的水里
我不希望成为
骤起骤落的浪花
却在想着
我能否成为
一个分子
融入大海这个家庭
共渡
走出尘嚣的门
蹚过一水之湄
我在阳光下
牵来一道彩虹
在夜里点燃渔火
照亮世间的昏暗
我不是岸上的花
不断绽放不断凋落
我没有流连湖泊和远山
只飘动在无边的湛蓝
我邀海鸥共舞
还在最低处
陪伴风帆远渡
罗春柏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歌作品见于国内多种名刊。有作品入选中国年度诗歌多种选本。诗集《枝头的绿羽》获广东省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