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方
2025-02-10 03:44
李 方
2025-02-10 03:44
两山夹一河的清水河河谷地带,野生动物是不多的。
兔子常见。下了夜雪,清晨能在积雪上看到它们留下的有如梅花的脚印,行迹曲里拐弯,可见在漫天飞雪中,它们觅食的艰难和犹疑。黄鼠是多的,提着水桶在野地里灌黄鼠是童年不多的乐趣之一,而在秋冬季发现了黄鼠洞,能掏出三五把粮食来。只有那些幸运的人,才能遭遇刺猬,看着它收缩了四条短腿蜷成一个刺球“滚开”。狼也是有的,但这块小平原距离东西两山差不多各有十多公里,除非大雪封山,狼饿急了,才会冒险下山,穿过山脚下的村庄和人家,突击到这片小平原上来,其他季节是很难见到的。
走兽不多,飞禽也相当有限。燕子、喜鹊、乌鸦这些普通的鸟儿随处可见。灰色的鹁鸽也有,飞得又高又远。还有一种鸟,土名叫沙鸡,和野鹁鸽体量相仿,它们不在这片小平原上生活,只在冬春季节,成群结队地飞过,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但是这种鸟显而易见不能高飞,而且眼神也不好,在沙尘天气里,顺着电线杆子走,运气好的话可以碰到被电线撞死的沙鸡。
数量庞大、气势恢宏的是麻雀,几乎无所不在。
它们,就是被枉杀者。因为它们啄食粮食,是掠食者。
糜、谷是耐旱的庄稼,属小秋杂粮,产量都不高,但特别适宜在清水河河谷种植。可恨的是,当它们颗粒饱满、垂下沉甸甸的穗头、行将成熟的时候,会有成群结队的麻雀,一片灰云似的,呼啦啦飞落下来,玩杂技一般覆满穗头,摇摇晃晃。它们每啄食一粒,同时会有数粒糜谷颗粒脱离穗头,撒落在地,这样损失的粮食不在少数。所以在“除四害”的时候,生产队专门派人手腕上架着鹞子各地巡察,放出去抓麻雀,使它们不能落地,或命丧黄泉。暑假期间半大小子所能干的事情,就是用弹弓袭扰它们。
我有一把非常精致的弹弓,是父亲为我做的。“丫”字支架是个天然的榆树的枝丫,被刨得异常光滑,两个“丫”端,还留着圆形的疙瘩,以防绑扎上去的皮条滑脱。由于经常被握,汗浸油渍,透出一种淡赭色的光泽。皮条是强力轮胎切割的,弹性很强,拉开它,需要咬牙切齿、弯腰皱眉凝聚双臂的力量。
我并不曾专门练习过打弹弓,所以没有准头。不过,满地都是麻雀,根本用不着瞄准,在皮套内夹上石子,拉开皮条,射出去完事。就这样随心所欲、毫无目标的一射,谷穗头上呼地腾起一片灰雾,忽左忽右,忽高忽低,麻雀大呼小叫,骤雨一般响彻谷地和天空;随即聚成一团,飞毯般飘向地边高大的白杨树,在那里吵成一片。再一弹射去,树冠中像是发生了爆炸,飞溅起无数的碎屑,越去越远,直至不见。
麻雀的天敌是鹞子,鹞子被网捕捉以后进行特别的训练,就成了人的帮手,成为了残害飞鸟的帮凶,但是这样的捕捉毕竟有限。大规模的捕杀麻雀,在我的记忆里,一种是鲁迅先生所描写的用“筛子”罩,往往很有效,雪后一个早晨的成绩,差不多可以得到一盘子麻雀肉。另一种是把麻雀引诱到密闭的狭小空间里去,比如一孔窑洞,或者废弃的房屋。我家就有一孔窑洞,窑洞里存放着糜子。为了通风,窑洞上的“哨眼”是开着的。耐心地观察,看到成群的麻雀通过“哨眼”进入窑洞后,用一团乱草堵住“哨眼”,打开窑门,迅速地进到窑洞里去,一个人拿着手电筒打出光柱,一个人空着两手只是抓,而满窑洞已经吃饱了糜子的麻雀,就在窑洞壁上乱撞,吵闹一片。每一个被捉住的麻雀,在手掌心里,急速地呼吸,那小小的温热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像此起彼伏的琴键撞击着手掌。
最辉煌的战果,是捉了半麻袋的麻雀。
我有一柄医用手术刀,异常锋利。麻雀是不用宰杀的,只需用两只手抓住它的尖嘴,把嘴从两边撕下去,一只完整的光溜溜的麻雀尸体就摊在地上了。手术刀主要是开膛破肚用的。
在那个时候,从心理上来说,人是没有多少罪孽感的,因为麻雀是“四害”之一。任何一种飞禽走兽,处在“时代运动”的暴风骤雨当中,它们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麻雀,再也不是早春枝头上的报春者,也不是清晨微曦里的报时者。一个时期,这些枉杀者的幸存者和后裔,确实是不见踪影了。
法布尔有一个观点:秋天了,庄稼成熟了。虫、鸟从四面八方赶来,取走上帝赐予它们的那部分食物。是的,粮食是人种的,这些鸟、虫没有动过一次手,也没有流过一滴汗,它们是不劳而获的掠食者。但它们,依然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把属于它们的食物搬运到自己的宅子里去。在它们眼里,这些粮食是自然长成的,是上苍赋予它们的。而人类,需要的哪一样食物,不是从自然中获得的呢?而提供原材料的自然,又是谁创造出来的呢?人类,是不是也是一个掠食者呢?
无论是生态也好,还是自然也罢,须知,飞禽走兽,芸芸众生,都是地球上的生物而已,都是宇宙中的一粒粒尘埃。
只有当弹弓成为一种玩具,而不是猎杀飞鸟的利器的时候,才可能实现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而每一个在黎明的鸟鸣声中醒来的人,都是幸福的。
两山夹一河的清水河河谷地带,野生动物是不多的。
兔子常见。下了夜雪,清晨能在积雪上看到它们留下的有如梅花的脚印,行迹曲里拐弯,可见在漫天飞雪中,它们觅食的艰难和犹疑。黄鼠是多的,提着水桶在野地里灌黄鼠是童年不多的乐趣之一,而在秋冬季发现了黄鼠洞,能掏出三五把粮食来。只有那些幸运的人,才能遭遇刺猬,看着它收缩了四条短腿蜷成一个刺球“滚开”。狼也是有的,但这块小平原距离东西两山差不多各有十多公里,除非大雪封山,狼饿急了,才会冒险下山,穿过山脚下的村庄和人家,突击到这片小平原上来,其他季节是很难见到的。
走兽不多,飞禽也相当有限。燕子、喜鹊、乌鸦这些普通的鸟儿随处可见。灰色的鹁鸽也有,飞得又高又远。还有一种鸟,土名叫沙鸡,和野鹁鸽体量相仿,它们不在这片小平原上生活,只在冬春季节,成群结队地飞过,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但是这种鸟显而易见不能高飞,而且眼神也不好,在沙尘天气里,顺着电线杆子走,运气好的话可以碰到被电线撞死的沙鸡。
数量庞大、气势恢宏的是麻雀,几乎无所不在。
它们,就是被枉杀者。因为它们啄食粮食,是掠食者。
糜、谷是耐旱的庄稼,属小秋杂粮,产量都不高,但特别适宜在清水河河谷种植。可恨的是,当它们颗粒饱满、垂下沉甸甸的穗头、行将成熟的时候,会有成群结队的麻雀,一片灰云似的,呼啦啦飞落下来,玩杂技一般覆满穗头,摇摇晃晃。它们每啄食一粒,同时会有数粒糜谷颗粒脱离穗头,撒落在地,这样损失的粮食不在少数。所以在“除四害”的时候,生产队专门派人手腕上架着鹞子各地巡察,放出去抓麻雀,使它们不能落地,或命丧黄泉。暑假期间半大小子所能干的事情,就是用弹弓袭扰它们。
我有一把非常精致的弹弓,是父亲为我做的。“丫”字支架是个天然的榆树的枝丫,被刨得异常光滑,两个“丫”端,还留着圆形的疙瘩,以防绑扎上去的皮条滑脱。由于经常被握,汗浸油渍,透出一种淡赭色的光泽。皮条是强力轮胎切割的,弹性很强,拉开它,需要咬牙切齿、弯腰皱眉凝聚双臂的力量。
我并不曾专门练习过打弹弓,所以没有准头。不过,满地都是麻雀,根本用不着瞄准,在皮套内夹上石子,拉开皮条,射出去完事。就这样随心所欲、毫无目标的一射,谷穗头上呼地腾起一片灰雾,忽左忽右,忽高忽低,麻雀大呼小叫,骤雨一般响彻谷地和天空;随即聚成一团,飞毯般飘向地边高大的白杨树,在那里吵成一片。再一弹射去,树冠中像是发生了爆炸,飞溅起无数的碎屑,越去越远,直至不见。
麻雀的天敌是鹞子,鹞子被网捕捉以后进行特别的训练,就成了人的帮手,成为了残害飞鸟的帮凶,但是这样的捕捉毕竟有限。大规模的捕杀麻雀,在我的记忆里,一种是鲁迅先生所描写的用“筛子”罩,往往很有效,雪后一个早晨的成绩,差不多可以得到一盘子麻雀肉。另一种是把麻雀引诱到密闭的狭小空间里去,比如一孔窑洞,或者废弃的房屋。我家就有一孔窑洞,窑洞里存放着糜子。为了通风,窑洞上的“哨眼”是开着的。耐心地观察,看到成群的麻雀通过“哨眼”进入窑洞后,用一团乱草堵住“哨眼”,打开窑门,迅速地进到窑洞里去,一个人拿着手电筒打出光柱,一个人空着两手只是抓,而满窑洞已经吃饱了糜子的麻雀,就在窑洞壁上乱撞,吵闹一片。每一个被捉住的麻雀,在手掌心里,急速地呼吸,那小小的温热的心脏在剧烈地跳动,像此起彼伏的琴键撞击着手掌。
最辉煌的战果,是捉了半麻袋的麻雀。
我有一柄医用手术刀,异常锋利。麻雀是不用宰杀的,只需用两只手抓住它的尖嘴,把嘴从两边撕下去,一只完整的光溜溜的麻雀尸体就摊在地上了。手术刀主要是开膛破肚用的。
在那个时候,从心理上来说,人是没有多少罪孽感的,因为麻雀是“四害”之一。任何一种飞禽走兽,处在“时代运动”的暴风骤雨当中,它们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麻雀,再也不是早春枝头上的报春者,也不是清晨微曦里的报时者。一个时期,这些枉杀者的幸存者和后裔,确实是不见踪影了。
法布尔有一个观点:秋天了,庄稼成熟了。虫、鸟从四面八方赶来,取走上帝赐予它们的那部分食物。是的,粮食是人种的,这些鸟、虫没有动过一次手,也没有流过一滴汗,它们是不劳而获的掠食者。但它们,依然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把属于它们的食物搬运到自己的宅子里去。在它们眼里,这些粮食是自然长成的,是上苍赋予它们的。而人类,需要的哪一样食物,不是从自然中获得的呢?而提供原材料的自然,又是谁创造出来的呢?人类,是不是也是一个掠食者呢?
无论是生态也好,还是自然也罢,须知,飞禽走兽,芸芸众生,都是地球上的生物而已,都是宇宙中的一粒粒尘埃。
只有当弹弓成为一种玩具,而不是猎杀飞鸟的利器的时候,才可能实现山清水秀,鸟语花香,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而每一个在黎明的鸟鸣声中醒来的人,都是幸福的。

-我已经到底线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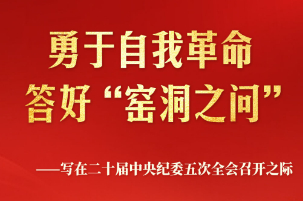



暂时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