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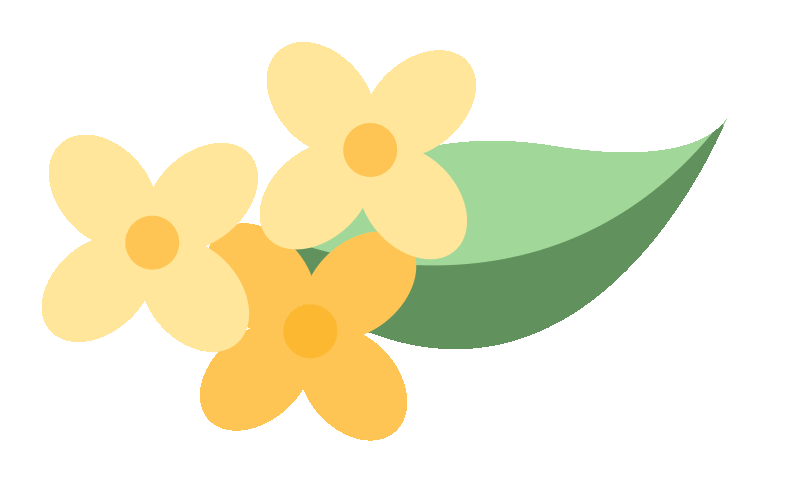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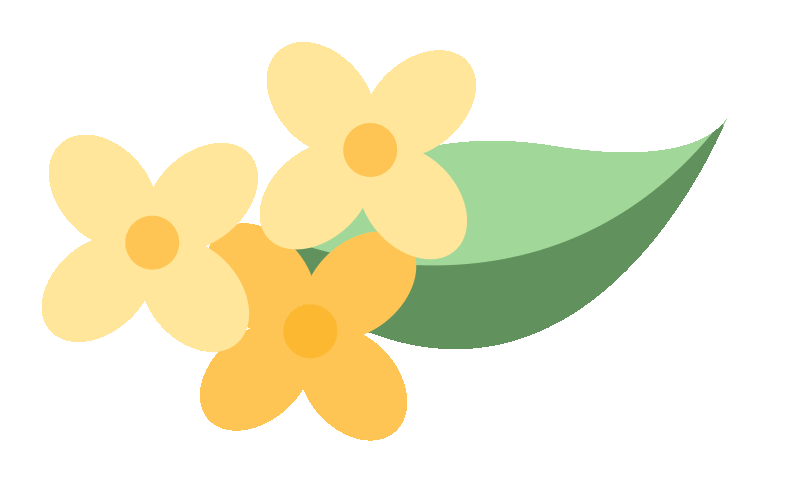
□方守金
珠三角大概没有摸秋的习俗,自皖居粤27年,我没听过当地人说过摸秋之事,也没读到相关文字。但在皖浙苏等地,摸秋却流传广远。清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说摸秋始于鸠兹(今芜湖),中秋月夜,初婚或适婚女子结伴出游,到瓜田里摘瓜,能生男孩。我打小就不信女子摘个瓜就能生男娃,总觉得那是找借口。还有,人们摸来的“秋”,除了瓜果,还有青菜、毛豆、玉米棒子等。
你城里生城里长,也能摸秋?能。我出生于淮南九龙岗矿,3岁举家迁到大通矿北侧的自来水厂家属院,而水厂则直属矿务局公用事业处,父亲在厂里干机修。50至70年代的百里煤城,若用今天的无人机航拍,会看到在滚滚淮河到繁阴素裹的舜耕山脉之间,有十多个大约方圆十几公里的矿厂及生活区,被更大面积的庄稼地及村落包围着,城乡交错。乡,由公社管辖;而矿区的路边、墙外乃至房前屋后的星散空地,任由人来种植了。当年,我们就摸这地儿的秋。
其实,我摸秋只有一次,可名气之大后果之严重,许久都是水厂大院之冠。那是1961年中秋节,天刚黑,两个十三四岁的哥,胳肢窝夹着青豆棵兴冲冲回到院内,撂在我们五户人家住的那排房下,立马获得一片夸奖,连我们兄妹涉嫌偷点东西就要抽树条的父母,也啧啧称赞。两个大孩受到鼓舞,说炮楼西边还有块豆地,再去。我尾随他俩也去了。这个五层高上面还有瞭望天台的水泥钢筋建筑,是日本人上世纪四十年代建造的,作为侵略罪证,已列为省级文物加围栏立标牌保护起来,如今是老大通唯一的地标建筑了,儿时印象老来闭眼就能在意识屏幕浮现的一切,都变样了或没有了。而摸秋年代,炮楼南是三号井和七号井为主体的大通煤矿,煤矿和炮楼之间是火车站;北边一条两车道公路挨着炮楼由西向东,路北三四十米,就是水厂和家属院。以炮楼为界,东边是平整的火车站货运站台,西边稀疏的几棵树下,尽是一块块庄稼地。那晚来摸的,就在这。
我跟在两个大孩子后边,望着他们从西边的田埂猫进豆地,嗖嗖地连枝带叶边拔青豆边往炮楼弯腰前进;炮楼近处是最高点,但有阴影,到那就可以绕炮楼半圈,大模大样回家去。我跟着弯腰用力拔了豆荚鼓鼓的一棵,攥在手里,前走两步拔第二棵时,谁知鬼使神差往南一看,浑身猛然打了个激灵。妈呀!三十多米外紧挨铁道的小房子开着窗,明亮的黄光下,一个大盖帽正往我这边看,吓得我扑通一下趴地上,盼着那人转过身去,我好爬起来往家跑。五分钟,也许十分钟过后,我悄悄侧过脸,透过庄稼和杂草的隙间,看到他转身是转身了,可一手拿起话筒,另一只手拨动起转盘来。坏喽!给公安局打电话了,怎么办?跑吧!我哆嗦着爬起来,没走两步,双腿打起软来,又扑通趴地上。
月亮升高了,大地一片澄明,而炮楼的阴影却回缩了。我恨这炮楼咋不再高它一两倍,如此,阴影伸过来就能逃了。我趴在湿润的豆地里,一动不敢动,四周散发着豆棵的清香,还有秋虫的吟唱,可这些不能抚慰我的极度恐慌。警察马上就要来了!手铐铮亮!老师说的抗日英雄被鬼子抓住,灌辣椒水坐老虎凳都英勇不屈。我英勇不了呀!会不会给我灌辣椒水?要是灌,请看我是个八九岁小孩,就灌一小口吧,最好放点油;老虎凳?不坐;坐凳上,老虎从后边伸出头张大嘴,啊呜、咔嚓……我身体紧贴地面,还是止不住两腿哆嗦,胡思乱想像条鞭子迅疾地在我脑子里抽过来掠过去。后来……后来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在家里的小床上。昨夜那两个抱豆回家的孩子都上床了,父母却不见二儿的踪影。父亲出门找,瞅了好几块地,才把熟睡的我抱回家。方师傅家的二小子,跑去摸秋在人家豆地里睡着了的故事,第二天就在厂里和家属院传开了,我成了焦点人物。瞌睡虫、胆小鬼!有人说,我就用细弱的声音辩解:不是,是小房里的人看到我了,他正给公安局打电话。记不清是大我两岁的哥哥,还是邻家大爷告诉我:哪是给公安局打电话,那是扳道工跟调度室打电话,他只管火车往哪个道上开,不管你拔豆的。我不信,自个儿来到这里,果然看到大盖帽不是打电话,而是大步流星赶到道岔口,把一个铁杆儿往怀里扳,火车轰隆隆开来,转个大弯往北去了;扳道工再把铁杆推回去,过来的火车就直直西行。我又羞又悔:连攥在手里的豆都没能带回家,这摸的,是哪门子的秋啊?
笑话几天就过去了,而我却口苦腹胀了半个月。本来,中秋节晚饭一个糖馍已吃饱,那年头工人家平日“杂以番薯……芋头之类”才能半饱,白面馒头只在年节才能吃上,所以一向尖馋的我,又撑了一个馍,趴在湿润的地里肠胃受了寒,肚子鼓胀得吓人。两三天了,家人看我还是吃不进排不出走不动上不了学,才重视起来。母亲把馒头烤成黑色的灰块,一天两次研磨冲半碗水让我喝,喝了七八天黑水,肠胃才正常起来。然而直到今天,一个甲子过去了,只要有别的主食,我一般不吃馒头。
转头想想,我这次摸秋,也并非一无所获:再好的饭菜不要吃到撑,再好的事情不能做过头。记住这教训,麻烦和痛苦会少些。美学上这叫不到顶点,生活上叫什么呢,不要做绝?

北山的慢时光 孟波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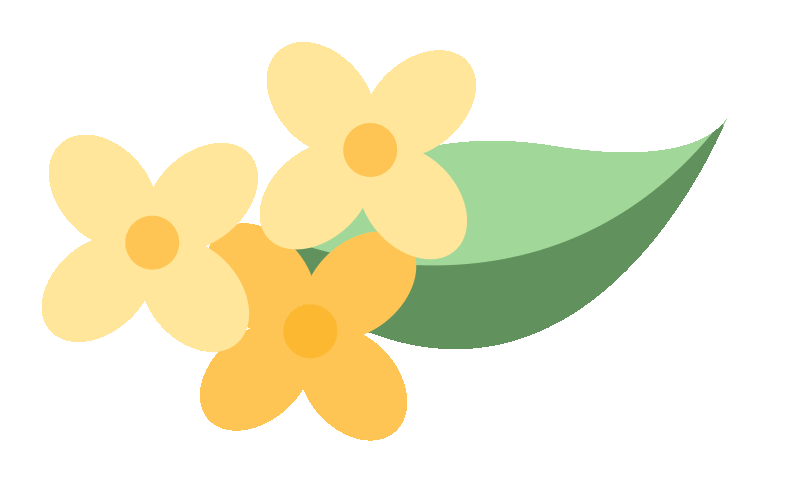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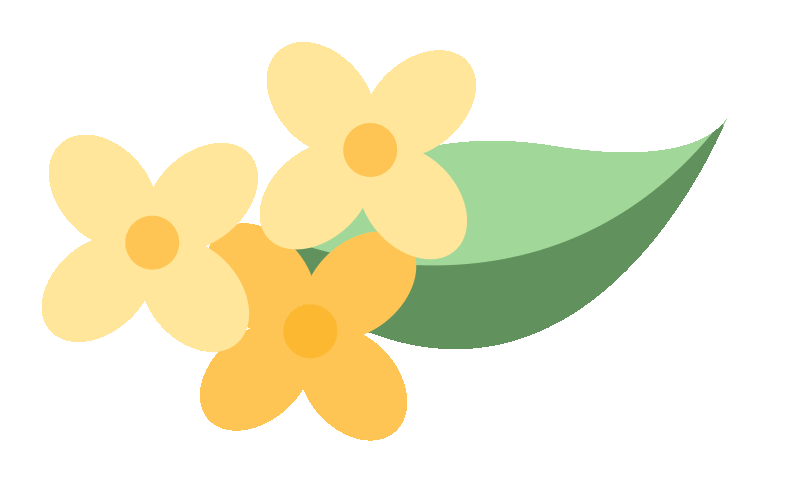
□张广超
青春编织的梦不曾释怀,像一壶烈酒越放越浓,它不算多姿多彩,却陪我度过浩如烟海的每个日夜,散发着岁月沉淀的甘甜。
回首自己走过的坎坷,心中不免有些惆怅。经过那残酷的“黑色七月”高考后,以几分之差落榜,多年的梦想就此破灭,痛苦与彷徨是免不了的。无意中,我翻开《摇着轮椅上北大》一书时,主人翁的奋进事迹,再一次让我看到黎明的一束光。
二十四年前,为了不让本不宽裕的家庭增加重负,我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背上简单的行囊,怀揣着对大都市的向往,独自踏上了南下广东的列车,决心到外面的世界追梦未来。
饭后,母亲忙着为我整理行囊。第一次离别,秋雨涟涟,空气里夹杂着瑟瑟的凉风,婆娑的思绪盘桓在逆村而行的小路上。我走出了母亲的视线,简单的行囊里打满了慈母对儿子的思念,即使翻越千山万水也走不出母亲呵护的视线,索性驻足从容地迎着村庄回眸一眼。
离别那天,妈妈再三叮属我:“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经过20多个小时的行程颠簸,我来到了广东顺德一个叫陈村的小镇上。在这陌生的小镇,一切都是那样新鲜,那样充满都市的气息。在姑父和二哥的安排下,我住进了他们简陋的工厂宿舍,这是一个简陋的工棚,屋内摆放有3张小床,心想如此窄小的空间怎么能住人呢?
或许是第一次远离家乡的不习惯,或许是蚊子的叮咬让我彻夜难眠。异乡夜空下只能仰望繁星,它们多像妈妈的眼睛注视着我。
我深知,找工作一定有很多困难,当时小镇上的工厂都是愿意招收经验丰富的员工,而我只是一个刚高中毕业的学生娃,没有一点优势。慢慢地我习惯了一次次被拒绝,一次次冷眼,像一朵飘摇的蒲公英附着在小镇的任意角落里。
一天,我陪同叔伯踏上了前往广州市的路,广州市也是我当时心中的远方。下车后,叔伯按照计划直接去了离车站不远的面试单位,而我却像只刚刚从牢笼里跑出的小羊羔在车站附近转悠,渴望寻得一根属于自己的绿草。
当走近一家小得可怜的中介求职所时,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让我无法拒绝,他们极力给我推荐一所技术学校,边介绍边讲解学校是如何的好,如何培养出一个个找到好工作的成功案例……
临近中午,中介所陆续来了很多同龄的求职者,或许都同我一样,在渴求学到一技之长的推动下,我们陆续登上了中介所组织开往一所技术学校的专车。也不知道车在陌生的道路上行进了多久,最终来到一座山坳里,一扇简陋的学校大门呈现在眼前。
通过参观、专业讲解,不知不觉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此时我心中不由得有些慌乱,担心如何能回到陈村小镇?于是我和司机沟通后,他爽快地答应我,愿意把我带到一个公交站点。可是到了站点一看,并不是我要停的站点。
无奈之下,我只好顺着一条小道独行,大约半小时后,终于到了一条江边,江边环境不错,草坪上有木椅,后来才知道这就是著名的珠江。
此时江风微微拂来,略带着一些凉意,八月的蚊虫还在疯狂地寻找着猎物。夜深了,没有一点睡意的我躺在稍宽的木椅上仰望星空。突然,从不远处射来一束刺眼的手电光,我赶忙坐起身,才发现是当地的巡警,我不由紧张起来,因为当天走得匆忙,什么证件也没有带。
巡警直奔我身边,用手电照在我身上打量着。用一种严厉的语气开始盘问:你是哪里人?为什么在这里躺着?有身份证、暂住证吗?一联串的质问,让我本就紧张的心情更加恐慌起来。我吱吱唔唔地小声回答着,生怕答错一个字。
夜是如此的安静。我站得笔直,用一双期盼的眼神看着他。或许,他并没有注意到我的眼神,直到他抽完一支烟后,和善地对我说:“小兄弟,我看你老实,相信你,你什么证件也没有带,晚上查得严,你就在这里原地呆着,不要乱走动,等天亮后向前走一公里,那里有个回陈村的车站。”
我长舒一口气,紧张慌乱的心终于平静下来。我不知道这位好心的巡警叫什么名字,但他暖心的话语一直回响在我心里,一直温暖着我的人生。
天色渐渐发白,珠江两岸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转眼已是深秋,正是全国各地征兵的季节,我手里捏着一封千里之外让我回家参军的家书。不当兵后悔一辈子,从军梦从小就根植在我的心里。第二天,我毅然踏上了返乡的列车。
锤炼,淬火,打磨,人生总是以这种方式打开,最后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时隔多年的一个满月,我依然手握钢枪,心怀赤诚,幻想着那柔软的月光便是母亲慈祥的目光。这个时候,四周一片宁静,只有月光静静地照在我的身上。

□郑智兴
在别处
在别处 是一种想念
那些缓缓经过的事物
是村边的小土狗悠哉地走过
是等待一树花在雨中的盛开
还有吹着芦笙长大的孩子
从隔帘飘落的琴声中
是汩汩流淌的光阴
在别处 是一种留恋
那些不经意间流露的善意
和来自远方真挚的祝福
经得起时间的沉淀
所有的美如同山岚
或许在山涧中随风散去
但会在晨曦的露珠中重生
在别处 你所接纳的
才是一种另有深意的人生
归来
1
远远的杨花飘到窗前
似暗香盈袖
我温一壶岁月的酒
摇醒尘封的记忆
有幽幽的笛声吹起
落花成阵
2
打捞起你清亮的笑声
从微光的角落
有珠玉的温润
如风铃的摇响
我一边拾掇
一边丢失
3
园中的桂子尚在
春水涨满门前干涸的小河
山风中的少年
以及水边的告白
流水已经带着落花飘远
屋外的青山是否记得?
4
华发尚未覆盖我的山顶
苍颜已经漫上了我的前额
那些渐渐失散的亲人
和你们深心的嘱托
注定只能在梦中闪现
相逢于岁月的尽头
5
我在离去 也在归来
我在旅途中获得宁静
在感怀中走向未来
我会随心停泊在一壶老酒中
我要缓缓地依偎在你的歌声里
火焰不曾燃烧的
曾希望有一段路可以伸延
延伸到可以有冷竣的思考
积攒起足够的勇气和耐心
坦然面对不确定的一切
比如 蜜蜂的刺
世俗无边的网
在没有路标的岔路口
随人群步入另一个方向
从此欢腾的是喧嚣而不是内心
反复折叠的是不成篇的诗行
时光带不回失联的问询
旗旌掀动的是虚空而不是力量
火焰不曾燃烧的
不会珍贵而绵长
相忘于江湖
悟出这行字的深意
是在几十载寒暑之后
当风雨桥上的斗转星移
在眼角刻下沧桑巨变
当所有旅伴的面目已经模糊
依然会闪现你清亮的眸子
困苦中共情的呐喊
不会改变沉沦的命运
唯有走出那段长长的峡谷险境
才有彼岸祝福的花朵
和可以承载未来的坦途
回望过去的一丝牵挂
不如在转身的时候
相忘于江湖
那么长久的隐疾
终将用人生之秋这帖药治愈
□刘云
南中国海,其实是一只蚌
中国蚌沿南中国岸一路
撒下珍珠串
珠海不大,正发亮
听海涛久了,我以为珠海
含着横琴吹响整个太平洋
南中国海新发表四个乐章
讲的都是中国四季故事
高潮部是一管横琴
独奏浪淘沙
有时横琴是一架古琴
琴声碾哭五千年岭南
有时是一只古螺
吹开一片年轻大海
口岸广场,时兴南中国方言
每日掀起横琴早晚潮
早潮是咖啡,晚潮是绿茶
怎么想天沐河都是横琴
一个过目不忘的门牌号码
挂在大陆社区大湾街道
横琴居委会雕花的大门
进出海天身影和神色
见面普通话,转身是粤语
横琴是南方琵琶,也是
北方辽阔的马头琴
粤先生和澳先生四手联奏它
大陆的乐迷和海洋的粉丝
簇拥中国大客厅大湾区大阳台
用整整一片太平洋的掌声和浪花
把横琴的窗口,装饰一新
□杨莲
使我们保持清醒
一个个跳跃的字符泛着光
标出人类的方向——
在虚实之间蔓延生长
被多少光芒抚摸过的风景
橱柜,琳琅满目的苍翠
一座满盛油墨气息的城堡
守住时光的掌纹
我安靜地汲取——
喜悦的灵魂,在这空间长存
遥远的人和事,穿越时空
变得紧凑、精炼
从书架的这头到那头
依旧不动声色,保持着神秘、高贵
走向你们,为了练习人类的技能
指挥家
当春天结束
高调的焰火便匆忙进入人们的日常
江河两岸,时雨时晴,搅动着夏季
如湖水荡漾的一排树
摇曳生姿的指挥家
在盛夏演绎最为深沉的呐喊
似乎要从灵魂深处
交出盛夏的果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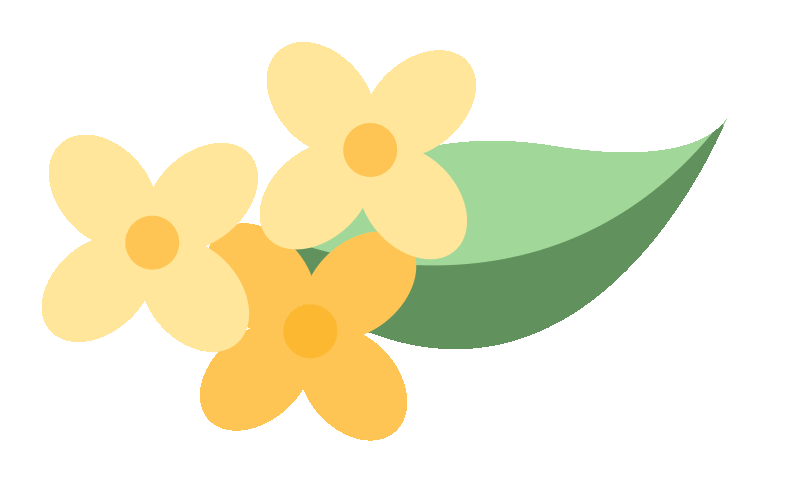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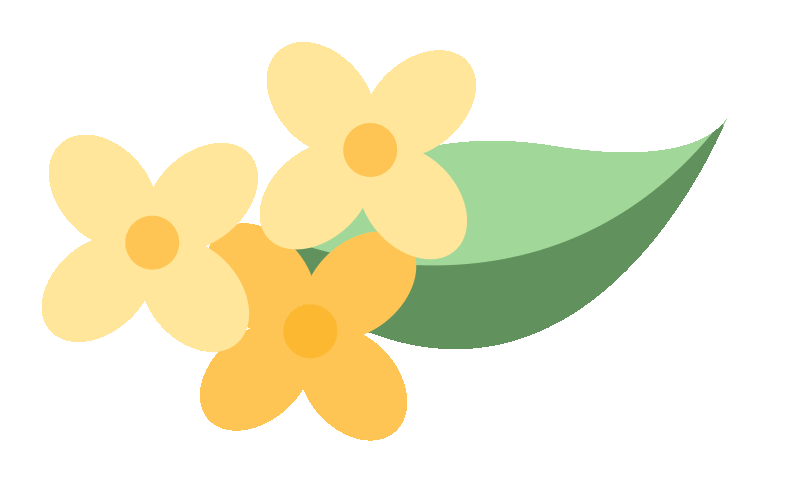
□方守金
珠三角大概没有摸秋的习俗,自皖居粤27年,我没听过当地人说过摸秋之事,也没读到相关文字。但在皖浙苏等地,摸秋却流传广远。清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说摸秋始于鸠兹(今芜湖),中秋月夜,初婚或适婚女子结伴出游,到瓜田里摘瓜,能生男孩。我打小就不信女子摘个瓜就能生男娃,总觉得那是找借口。还有,人们摸来的“秋”,除了瓜果,还有青菜、毛豆、玉米棒子等。
你城里生城里长,也能摸秋?能。我出生于淮南九龙岗矿,3岁举家迁到大通矿北侧的自来水厂家属院,而水厂则直属矿务局公用事业处,父亲在厂里干机修。50至70年代的百里煤城,若用今天的无人机航拍,会看到在滚滚淮河到繁阴素裹的舜耕山脉之间,有十多个大约方圆十几公里的矿厂及生活区,被更大面积的庄稼地及村落包围着,城乡交错。乡,由公社管辖;而矿区的路边、墙外乃至房前屋后的星散空地,任由人来种植了。当年,我们就摸这地儿的秋。
其实,我摸秋只有一次,可名气之大后果之严重,许久都是水厂大院之冠。那是1961年中秋节,天刚黑,两个十三四岁的哥,胳肢窝夹着青豆棵兴冲冲回到院内,撂在我们五户人家住的那排房下,立马获得一片夸奖,连我们兄妹涉嫌偷点东西就要抽树条的父母,也啧啧称赞。两个大孩受到鼓舞,说炮楼西边还有块豆地,再去。我尾随他俩也去了。这个五层高上面还有瞭望天台的水泥钢筋建筑,是日本人上世纪四十年代建造的,作为侵略罪证,已列为省级文物加围栏立标牌保护起来,如今是老大通唯一的地标建筑了,儿时印象老来闭眼就能在意识屏幕浮现的一切,都变样了或没有了。而摸秋年代,炮楼南是三号井和七号井为主体的大通煤矿,煤矿和炮楼之间是火车站;北边一条两车道公路挨着炮楼由西向东,路北三四十米,就是水厂和家属院。以炮楼为界,东边是平整的火车站货运站台,西边稀疏的几棵树下,尽是一块块庄稼地。那晚来摸的,就在这。
我跟在两个大孩子后边,望着他们从西边的田埂猫进豆地,嗖嗖地连枝带叶边拔青豆边往炮楼弯腰前进;炮楼近处是最高点,但有阴影,到那就可以绕炮楼半圈,大模大样回家去。我跟着弯腰用力拔了豆荚鼓鼓的一棵,攥在手里,前走两步拔第二棵时,谁知鬼使神差往南一看,浑身猛然打了个激灵。妈呀!三十多米外紧挨铁道的小房子开着窗,明亮的黄光下,一个大盖帽正往我这边看,吓得我扑通一下趴地上,盼着那人转过身去,我好爬起来往家跑。五分钟,也许十分钟过后,我悄悄侧过脸,透过庄稼和杂草的隙间,看到他转身是转身了,可一手拿起话筒,另一只手拨动起转盘来。坏喽!给公安局打电话了,怎么办?跑吧!我哆嗦着爬起来,没走两步,双腿打起软来,又扑通趴地上。
月亮升高了,大地一片澄明,而炮楼的阴影却回缩了。我恨这炮楼咋不再高它一两倍,如此,阴影伸过来就能逃了。我趴在湿润的豆地里,一动不敢动,四周散发着豆棵的清香,还有秋虫的吟唱,可这些不能抚慰我的极度恐慌。警察马上就要来了!手铐铮亮!老师说的抗日英雄被鬼子抓住,灌辣椒水坐老虎凳都英勇不屈。我英勇不了呀!会不会给我灌辣椒水?要是灌,请看我是个八九岁小孩,就灌一小口吧,最好放点油;老虎凳?不坐;坐凳上,老虎从后边伸出头张大嘴,啊呜、咔嚓……我身体紧贴地面,还是止不住两腿哆嗦,胡思乱想像条鞭子迅疾地在我脑子里抽过来掠过去。后来……后来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在家里的小床上。昨夜那两个抱豆回家的孩子都上床了,父母却不见二儿的踪影。父亲出门找,瞅了好几块地,才把熟睡的我抱回家。方师傅家的二小子,跑去摸秋在人家豆地里睡着了的故事,第二天就在厂里和家属院传开了,我成了焦点人物。瞌睡虫、胆小鬼!有人说,我就用细弱的声音辩解:不是,是小房里的人看到我了,他正给公安局打电话。记不清是大我两岁的哥哥,还是邻家大爷告诉我:哪是给公安局打电话,那是扳道工跟调度室打电话,他只管火车往哪个道上开,不管你拔豆的。我不信,自个儿来到这里,果然看到大盖帽不是打电话,而是大步流星赶到道岔口,把一个铁杆儿往怀里扳,火车轰隆隆开来,转个大弯往北去了;扳道工再把铁杆推回去,过来的火车就直直西行。我又羞又悔:连攥在手里的豆都没能带回家,这摸的,是哪门子的秋啊?
笑话几天就过去了,而我却口苦腹胀了半个月。本来,中秋节晚饭一个糖馍已吃饱,那年头工人家平日“杂以番薯……芋头之类”才能半饱,白面馒头只在年节才能吃上,所以一向尖馋的我,又撑了一个馍,趴在湿润的地里肠胃受了寒,肚子鼓胀得吓人。两三天了,家人看我还是吃不进排不出走不动上不了学,才重视起来。母亲把馒头烤成黑色的灰块,一天两次研磨冲半碗水让我喝,喝了七八天黑水,肠胃才正常起来。然而直到今天,一个甲子过去了,只要有别的主食,我一般不吃馒头。
转头想想,我这次摸秋,也并非一无所获:再好的饭菜不要吃到撑,再好的事情不能做过头。记住这教训,麻烦和痛苦会少些。美学上这叫不到顶点,生活上叫什么呢,不要做绝?

北山的慢时光 孟波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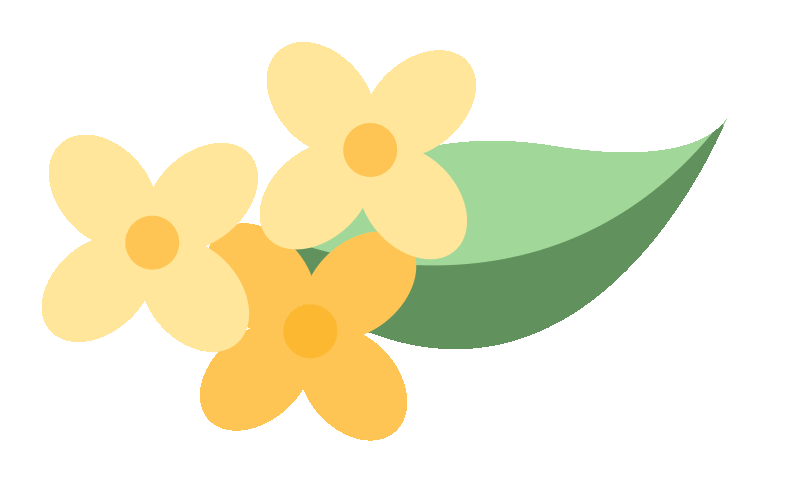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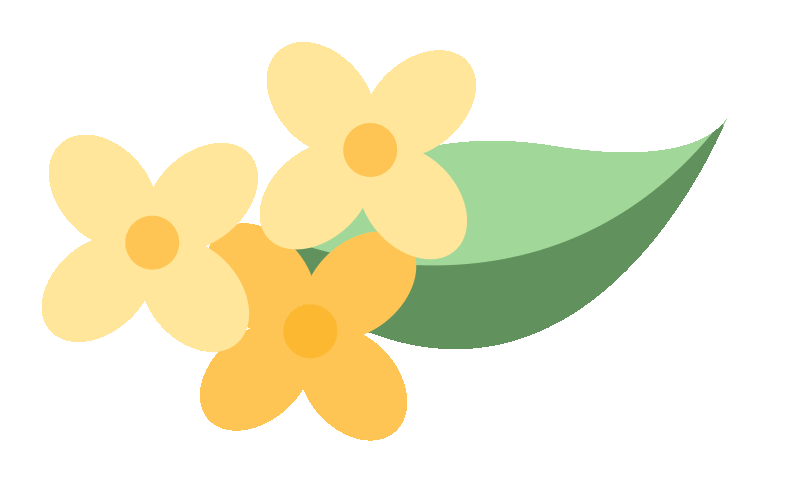
□张广超
青春编织的梦不曾释怀,像一壶烈酒越放越浓,它不算多姿多彩,却陪我度过浩如烟海的每个日夜,散发着岁月沉淀的甘甜。
回首自己走过的坎坷,心中不免有些惆怅。经过那残酷的“黑色七月”高考后,以几分之差落榜,多年的梦想就此破灭,痛苦与彷徨是免不了的。无意中,我翻开《摇着轮椅上北大》一书时,主人翁的奋进事迹,再一次让我看到黎明的一束光。
二十四年前,为了不让本不宽裕的家庭增加重负,我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背上简单的行囊,怀揣着对大都市的向往,独自踏上了南下广东的列车,决心到外面的世界追梦未来。
饭后,母亲忙着为我整理行囊。第一次离别,秋雨涟涟,空气里夹杂着瑟瑟的凉风,婆娑的思绪盘桓在逆村而行的小路上。我走出了母亲的视线,简单的行囊里打满了慈母对儿子的思念,即使翻越千山万水也走不出母亲呵护的视线,索性驻足从容地迎着村庄回眸一眼。
离别那天,妈妈再三叮属我:“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经过20多个小时的行程颠簸,我来到了广东顺德一个叫陈村的小镇上。在这陌生的小镇,一切都是那样新鲜,那样充满都市的气息。在姑父和二哥的安排下,我住进了他们简陋的工厂宿舍,这是一个简陋的工棚,屋内摆放有3张小床,心想如此窄小的空间怎么能住人呢?
或许是第一次远离家乡的不习惯,或许是蚊子的叮咬让我彻夜难眠。异乡夜空下只能仰望繁星,它们多像妈妈的眼睛注视着我。
我深知,找工作一定有很多困难,当时小镇上的工厂都是愿意招收经验丰富的员工,而我只是一个刚高中毕业的学生娃,没有一点优势。慢慢地我习惯了一次次被拒绝,一次次冷眼,像一朵飘摇的蒲公英附着在小镇的任意角落里。
一天,我陪同叔伯踏上了前往广州市的路,广州市也是我当时心中的远方。下车后,叔伯按照计划直接去了离车站不远的面试单位,而我却像只刚刚从牢笼里跑出的小羊羔在车站附近转悠,渴望寻得一根属于自己的绿草。
当走近一家小得可怜的中介求职所时,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让我无法拒绝,他们极力给我推荐一所技术学校,边介绍边讲解学校是如何的好,如何培养出一个个找到好工作的成功案例……
临近中午,中介所陆续来了很多同龄的求职者,或许都同我一样,在渴求学到一技之长的推动下,我们陆续登上了中介所组织开往一所技术学校的专车。也不知道车在陌生的道路上行进了多久,最终来到一座山坳里,一扇简陋的学校大门呈现在眼前。
通过参观、专业讲解,不知不觉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此时我心中不由得有些慌乱,担心如何能回到陈村小镇?于是我和司机沟通后,他爽快地答应我,愿意把我带到一个公交站点。可是到了站点一看,并不是我要停的站点。
无奈之下,我只好顺着一条小道独行,大约半小时后,终于到了一条江边,江边环境不错,草坪上有木椅,后来才知道这就是著名的珠江。
此时江风微微拂来,略带着一些凉意,八月的蚊虫还在疯狂地寻找着猎物。夜深了,没有一点睡意的我躺在稍宽的木椅上仰望星空。突然,从不远处射来一束刺眼的手电光,我赶忙坐起身,才发现是当地的巡警,我不由紧张起来,因为当天走得匆忙,什么证件也没有带。
巡警直奔我身边,用手电照在我身上打量着。用一种严厉的语气开始盘问:你是哪里人?为什么在这里躺着?有身份证、暂住证吗?一联串的质问,让我本就紧张的心情更加恐慌起来。我吱吱唔唔地小声回答着,生怕答错一个字。
夜是如此的安静。我站得笔直,用一双期盼的眼神看着他。或许,他并没有注意到我的眼神,直到他抽完一支烟后,和善地对我说:“小兄弟,我看你老实,相信你,你什么证件也没有带,晚上查得严,你就在这里原地呆着,不要乱走动,等天亮后向前走一公里,那里有个回陈村的车站。”
我长舒一口气,紧张慌乱的心终于平静下来。我不知道这位好心的巡警叫什么名字,但他暖心的话语一直回响在我心里,一直温暖着我的人生。
天色渐渐发白,珠江两岸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转眼已是深秋,正是全国各地征兵的季节,我手里捏着一封千里之外让我回家参军的家书。不当兵后悔一辈子,从军梦从小就根植在我的心里。第二天,我毅然踏上了返乡的列车。
锤炼,淬火,打磨,人生总是以这种方式打开,最后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时隔多年的一个满月,我依然手握钢枪,心怀赤诚,幻想着那柔软的月光便是母亲慈祥的目光。这个时候,四周一片宁静,只有月光静静地照在我的身上。

□郑智兴
在别处
在别处 是一种想念
那些缓缓经过的事物
是村边的小土狗悠哉地走过
是等待一树花在雨中的盛开
还有吹着芦笙长大的孩子
从隔帘飘落的琴声中
是汩汩流淌的光阴
在别处 是一种留恋
那些不经意间流露的善意
和来自远方真挚的祝福
经得起时间的沉淀
所有的美如同山岚
或许在山涧中随风散去
但会在晨曦的露珠中重生
在别处 你所接纳的
才是一种另有深意的人生
归来
1
远远的杨花飘到窗前
似暗香盈袖
我温一壶岁月的酒
摇醒尘封的记忆
有幽幽的笛声吹起
落花成阵
2
打捞起你清亮的笑声
从微光的角落
有珠玉的温润
如风铃的摇响
我一边拾掇
一边丢失
3
园中的桂子尚在
春水涨满门前干涸的小河
山风中的少年
以及水边的告白
流水已经带着落花飘远
屋外的青山是否记得?
4
华发尚未覆盖我的山顶
苍颜已经漫上了我的前额
那些渐渐失散的亲人
和你们深心的嘱托
注定只能在梦中闪现
相逢于岁月的尽头
5
我在离去 也在归来
我在旅途中获得宁静
在感怀中走向未来
我会随心停泊在一壶老酒中
我要缓缓地依偎在你的歌声里
火焰不曾燃烧的
曾希望有一段路可以伸延
延伸到可以有冷竣的思考
积攒起足够的勇气和耐心
坦然面对不确定的一切
比如 蜜蜂的刺
世俗无边的网
在没有路标的岔路口
随人群步入另一个方向
从此欢腾的是喧嚣而不是内心
反复折叠的是不成篇的诗行
时光带不回失联的问询
旗旌掀动的是虚空而不是力量
火焰不曾燃烧的
不会珍贵而绵长
相忘于江湖
悟出这行字的深意
是在几十载寒暑之后
当风雨桥上的斗转星移
在眼角刻下沧桑巨变
当所有旅伴的面目已经模糊
依然会闪现你清亮的眸子
困苦中共情的呐喊
不会改变沉沦的命运
唯有走出那段长长的峡谷险境
才有彼岸祝福的花朵
和可以承载未来的坦途
回望过去的一丝牵挂
不如在转身的时候
相忘于江湖
那么长久的隐疾
终将用人生之秋这帖药治愈
□刘云
南中国海,其实是一只蚌
中国蚌沿南中国岸一路
撒下珍珠串
珠海不大,正发亮
听海涛久了,我以为珠海
含着横琴吹响整个太平洋
南中国海新发表四个乐章
讲的都是中国四季故事
高潮部是一管横琴
独奏浪淘沙
有时横琴是一架古琴
琴声碾哭五千年岭南
有时是一只古螺
吹开一片年轻大海
口岸广场,时兴南中国方言
每日掀起横琴早晚潮
早潮是咖啡,晚潮是绿茶
怎么想天沐河都是横琴
一个过目不忘的门牌号码
挂在大陆社区大湾街道
横琴居委会雕花的大门
进出海天身影和神色
见面普通话,转身是粤语
横琴是南方琵琶,也是
北方辽阔的马头琴
粤先生和澳先生四手联奏它
大陆的乐迷和海洋的粉丝
簇拥中国大客厅大湾区大阳台
用整整一片太平洋的掌声和浪花
把横琴的窗口,装饰一新
□杨莲
使我们保持清醒
一个个跳跃的字符泛着光
标出人类的方向——
在虚实之间蔓延生长
被多少光芒抚摸过的风景
橱柜,琳琅满目的苍翠
一座满盛油墨气息的城堡
守住时光的掌纹
我安靜地汲取——
喜悦的灵魂,在这空间长存
遥远的人和事,穿越时空
变得紧凑、精炼
从书架的这头到那头
依旧不动声色,保持着神秘、高贵
走向你们,为了练习人类的技能
指挥家
当春天结束
高调的焰火便匆忙进入人们的日常
江河两岸,时雨时晴,搅动着夏季
如湖水荡漾的一排树
摇曳生姿的指挥家
在盛夏演绎最为深沉的呐喊
似乎要从灵魂深处
交出盛夏的果实




暂时没有评论